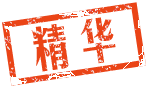第二十一章 · 渡口血战
7 A, V5 U$ E$ p- f- d% _ U6 j w, I6 t& e0 P3 M0 p/ f9 h
雨,不是下的,是倒的。 天与地之间,被一道厚重无比的水幕连接,豆大的雨点砸在江面上,激起千万朵破碎的白莲。砸在泥土里,溅起浑浊的浪花。雷声在乌云深处翻滚,像一头被囚禁的巨兽,每一次不甘的咆哮,都伴随着一道撕裂天穹的惨白闪电。 安澜渡,已是人间炼狱。 车三爷退到了最后,脸上那志在必得的狞笑,在风雨中显得有些扭曲。他的刀手们,如同一群被血腥味刺激的野狗,从四面八方扑向那三个被围困在中央的人。 老卒(盾)没有动。他只是将李四爷死死地护在身后,身体微弓,像一块嵌入大地的礁石。雨水顺着他刚硬的脸部轮廓流下,眼神却比这江水更加冰冷。他的面前,是那辆被遗弃的马车,此刻成了他唯一的掩体。 “刃!”他发出一声低吼。 这声吼,不是命令,是释放枷锁的信号。 昆仑奴(刃)动了。 他没有武器,他的身体就是最可怕的武器。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黑豹,不退反进,迎着最密集的人潮,悍然撞了进去。 “噗!” 最前面的一个刀手,根本没看清他的动作,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撞在胸口,肋骨碎裂的声音被淹没在雷鸣中,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,撞倒了身后的一片同伙。 昆仑奴的拳、肘、膝,变成了最简洁、最致命的杀人工具。没有花哨的招式,只有最原始的力量和速度。一拳击碎喉骨,一肘捣烂心窝,一记膝撞顶断脊椎。鲜血刚一喷出,便被瓢泼大雨冲刷、稀释,在泥泞的地面上汇成一条条暗红色的溪流。 他是一把只攻不守的刀,用自己的身体,在刀阵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缺口。 但敌人太多了。 一把长刀,趁着昆仑奴击杀另一人的间隙,阴险地从侧后方捅向他的腰肋。 “铛!” 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。 是老卒。他不知何时,已经从马车上拆下了一扇车门,如同一面小盾,精准地挡在了昆仑奴的身侧。木制的车门被刀锋劈开,但终究是为昆仑奴争取了那毫秒之间。 昆仑奴头也不回,反手一抓,精准地扣住了那名刀手的手腕,用力一拧! “咔嚓!” 骨头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。在刀手凄厉的惨嚎中,昆仑奴夺过他的刀,反手一挥,一颗头颅伴随着血雨,冲天而起。 有了刀的昆仑奴,化身为真正的修罗。刀光在雨幕中织成一张死亡之网,每一次闪烁,都伴随着生命的凋零。 然而,双拳难敌四手。老卒用那扇破烂的车门,挡开了两支射向李四爷的冷箭,自己的肩头,却被另一把刀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李四爷也拔刀在手,背靠着老卒,勉力抵挡,但这位养尊处优的龙头,早已不复当年之勇,几招下来,已是险象环生。 车三爷看着这一切,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他知道,这两个人再能打,也不过是笼中困兽,力气总有用尽的时候。他对着身边的亲信使了个眼色,几名最精锐的刀手,悄然后退,准备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,发动最后的雷霆一击。 “结束了。”车三爷喃喃自语。
$ ?7 O$ V# I7 `' n: G0 E0 A' x
& P6 t8 t3 h3 k/ K1 s哨塔上,阿目(眼)放下了千里镜。雨太大,镜片早已模糊不清。但他不需要看了。下面的战局,他用心都能推演出来。任务,失败了。 他转身准备离去。定金到手,没必要再掺和。这是他一贯的原则。 可就在他转身的刹那,他的余光,瞥见了芦苇荡的另一侧。那里停着一艘不起眼的小船,车三爷的几名亲信,正护着他,悄悄地朝那艘船移动。 阿目的脚步,停住了。 他不是为了什么团队情谊。他只是想起了老瓷匠的规矩:“有始有终。”任务失败,坏的是他“眼”的名声。更重要的是,车三爷这种人,一旦得势,必然会斩草除根。今天这里所有知情的人,包括他自己,都将成为被追杀的目标。 他的独眼里,闪过一丝冷酷的决断。 他从怀里,摸出了一件东西。不是什么暗器,而是一枚磨得锋利无比的铜钱。那是他赌坊里的朋友教他的消遣玩意儿。 他没有瞄准车三爷本人。太远,风雨太大,没有把握。他瞄准的,是那艘小船的船篷顶上,悬挂着的一盏用来照明的铁皮灯笼。 阿目深吸一口气,手臂猛地一挥。 铜钱在雨幕中,划出一道微不可见的轨迹,带着尖锐的呼啸声,精准地击中了那盏灯笼的挂钩。 “当啷!” 沉重的铁皮灯笼,脱钩坠落,不偏不倚,正好砸在一名准备跳上船的刀手头上。那名刀手闷哼一声,翻身落水。更重要的是,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车三爷的撤退计划,彻底暴露在了老卒的视野里。
; O, p s v( @; X. l0 S) E
" o( S4 L/ P7 N2 Y0 I% @) b) {
江心,十三娘(影)的乌篷船像一片无助的叶子,在风浪中摇曳。她已经撑船到了安全距离。岸上的生死,与她无关。 她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然而,她的目光,却被另一艘从下游芦苇丛中悄然驶出的小船吸引了。那艘船,直奔江心而来,显然是准备接应什么人。 十三娘的眉头,微微蹙起。她看到了船上那个满脸狞笑、指挥若定的身影——车三爷。 一股冰冷的杀意,从她心底升起。 不是为了报仇,也不是为了同伴。她只是单纯地觉得,这个男人,是个麻烦。他今天能设局背叛,明天就能为了灭口,追杀到天涯海角。她渴望的安宁生活,绝不能被这种阴魂不散的威胁所笼罩。 斩草,就要除根。这是她在皇宫里学到的第一条生存法则。 她从发髻中,取下一根细如牛毛的银针。针尖在昏暗的船舱里,闪着幽蓝色的光。 她将银针含入一个极细的竹管中,趴在船篷的缝隙里,像一只最耐心的猎手,等待着时机。 ) j% z2 I' e, g+ m6 U
8 H/ E$ x: D3 F% O( W% Z; H( _# _
岸上,老卒看到了车三爷的动向。他立刻明白了阿目的意图。 “刃!斩首!”老卒用尽全身力气,将手中的破烂车门,狠狠地掷了出去。车门在空中旋转,撞开了一条通往车三爷的短暂通道。 昆仑奴心领神会。他不再与杂兵缠斗,脚下在泥泞中猛地一踏,溅起一片泥水,整个人如炮弹般,沿着老卒为他打开的线路,直冲车三爷而去。 车三爷大惊失色,身边的亲信连忙上前阻拦。 但他们面对的,是一把已经出鞘、再无任何顾忌的绝世凶刃。 刀光一闪,两名亲信的身体,从腰部被整齐地斩断。 车三爷吓得魂飞魄散,转身就想跳上另一艘接应的船。 可他刚一转身,就感觉脖子猛地一凉,仿佛被一只蚊子,轻轻地叮了一下。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,却什么也没摸到。一股麻痹感,迅速从他的脖颈,蔓延至全身。他的身体,瞬间僵住,脸上的惊恐,凝固成一个永恒的表情。 “噗通。” 他像一截木桩,直挺挺地倒了下去,溅起一圈泥水。 而昆仑奴的刀,也恰在此时,到了。 刀锋落下,一颗大好头颅,滚落在泥水之中。 旱码头的霸主,车三爷,死。 主帅一死,剩下的刀手们顿时乱作一团,再无战心,怪叫着四散奔逃。 风雨依旧,渡口边,只剩下三个浑身浴血的人,和满地的尸体。 老卒拄着刀,半跪在地,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昆仑奴站在他身边,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。李四爷瘫坐在泥水里,望着车三爷的无头尸体,失魂落魄。 战斗,结束了。
+ E- v$ G" I8 h* _# T
- n: S1 f5 e( r/ O3 W1 n
第二十二章 · 最后的晚餐
( L/ y/ r! ~% ]% Q; g, l
4 V$ i! p' x' ?2 T, z& T1 W三更天,雨停了。 洛阳城南,一家只在深夜开张的羊汤馆。老板是个瘸腿的老头,店里只有三张桌子,一盏昏黄的油灯,将墙壁上被油烟熏出的斑驳痕迹,照得影影绰绰。 五郎(手)就坐在最里面的那张桌子旁。 他面前,是一碗已经冷掉的羊汤。他没有动。他只是静静地坐着,像是在等待什么。他知道,他们会来。这是“规矩”。 门帘被掀开,两个人走了进来。 是老卒和昆仑奴。 他们换了干净的衣服,但身上那股尚未散尽的血腥味和煞气,让瘸腿老板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 老卒没有看五郎,只是对着老板,伸出三根手指。 “三碗汤,半斤饼。”他的声音沙哑,带着一丝疲惫。 瘸腿老板不敢多问,连忙转身去忙活。 老卒和昆仑奴,在五郎的对面坐了下来。三个人,谁也没有说话。空气中,只有灶膛里柴火的哔剥声,和羊汤在锅里翻滚的“咕嘟”声。 很快,三碗滚烫的羊汤,一盘烙得焦黄的饼,被端了上来。 老卒拿起一块饼,掰成两半,将一半递给昆仑奴,另一半自己留下。然后,他拿起勺子,开始喝汤。 他的动作,依旧是一丝不苟。每一口汤,每一口饼,都像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。 昆仑奴学着他的样子,沉默地吃着。 五郎也终于动了。他将面前那碗冷掉的汤推到一旁,端起热汤,也开始喝。他吃得很慢,很认真,仿佛在品尝人间最后的美味。 一顿饭,在极致的沉默中进行。 没有质问,没有辩解。 背叛,已经发生。后果,必须承担。 这一切,早已超越了对错,只剩下“规矩”二字。 五郎吃完了最后一口饼,喝完了最后一口汤。他抬起头,第一次正视老卒的眼睛。他的眼神里,没有恐惧,也没有悔恨,只有一种解脱般的平静。 “白马寺那个孩子,”五郎的声音很轻,“我把所有的钱,都留给了他。” 老卒咀嚼的动作,停顿了一下。但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继续将嘴里的饼,咽了下去。 五郎笑了笑,像是在自嘲。 “我师父说,‘盗亦有道’。我只是……想守住我自己的‘道’。” 他说完,不再言语。 老卒也吃完了。他从怀里,摸出一样东西,轻轻地放在桌上,推到五郎面前。 那是一枚金叶子。 是这次任务,原本属于五郎的那一份酬劳。 收钱办事,有始有终。即便你背叛了,但你的那一份工,也算到了此刻。这是老卒的“规矩”。 五郎看着那枚在油灯下闪着光芒的金叶子,眼神复杂。他最终还是伸出手,将它收进了怀里。 “谢谢。”他说。 老卒站起身,昆仑奴也随之站起。他们付了钱,没有回头,掀开门帘,走进了外面清冷的夜色中。 羊汤馆里,只剩下五郎一个人。 他坐在那里,一动不动,像一尊雕像。 许久,他忽然低下头,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一口暗红色的鲜血,从他口中喷出,染红了面前的桌子。 是十三娘的针。 那根在渡口射中车三爷的淬毒银针,在穿透车三爷的脖颈后,余势未衰,扎进了他身后不远处的,五郎的胸口。针细如牛毛,入肉无痕,当时的他,只以为是被雨滴打中。 这毒,不会立刻发作。它会随着血液,慢慢侵入五脏六腑。在一次剧烈的气血涌动后,彻底爆发。 而刚才那顿饭,就是最后的催命符。 五郎趴在桌子上,身体不住地抽搐。他的意识,在迅速地消散。恍惚间,他仿佛又看到了棺材铺后院那个抱着冷馒头的孩子,看到了师父临死前那双不甘的眼睛。 他嘴唇蠕动,似乎想说什么,却最终没能发出任何声音。 生命,如同一盏油尽的灯,悄然熄灭。 瘸腿老板从后厨探出头,看到这一幕,吓得魂飞魄散。但他最终只是叹了口气,走上前,用一块抹布,默默地擦拭着桌上的血迹。 在这座城市的阴影里,生死,早已是寻常。 , @9 P5 n' d1 F# r, e2 |- W: m) @2 \
2 \! z2 q' j, y! f3 x第二十三章 · 余烬
* w, k' @) u" T# N$ i
( _' Y( b9 n, ?$ h
3 d& S* i# v3 ^" f; @# t
, P+ ~) z+ I- m- v) q盾 三天后,洛阳城门。 老卒换上了一身寻常百姓的衣服,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。他回头,深深地望了一眼这座雄伟的都城。 他赢了。他用自己的“规矩”,战胜了所有的混乱和背叛。可他的心里,却空荡荡的。 那晚,在那家深夜的羊汤馆里,当他放下那枚代表契约的金叶子时,也一并将那面伴随自己多年的、残破的护心镜,留在了桌上。 当他走出羊汤馆的那一刻,他便放下了。放下了朔方军副尉的荣光,也放下了兵败被黜的耻辱。他终于明白,他偏执信奉的“规矩”,不过是一座囚禁自己的牢笼。 他不会再回军队,也不会再当什么保镖。 他只是想去走走。去看看那些没有规矩的山,没有秩序的水。 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童,追着一只滚动的木球,从他身边跑过,摔了一跤,哇哇大哭。他的母亲笑着跑过来,将他抱起,拍了拍他身上的土。 老卒看着这一幕,那张万年冰封的脸上,线条似乎柔和了一些。他转过身,迎着朝阳,走出了城门,汇入了通往远方的官道。他的背影,不再像一杆标枪,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,再也无人能记起的旅人。 眼 “三碗不过岗”茶肆,依旧是那个昏昏欲睡的午后。 阿目坐在老位置,面前一碗粗茶,一碟茴香豆。伙计还在打盹,苍蝇还在飞。一切,仿佛从未改变。 他拿到了剩下的酬劳,还有车三爷留在船上的全部财物——那是十三娘托船家捎给他的讯息,作为他那记“铜钱示警”的报答。 他现在很有钱,足以让他离开这里,去追查那个毁了他一切的仇人。 但他没有走。 他只是坐着,用他那只独眼,冷静地看着窗外的一切。卖炊饼的妇人,卖字画的书生,形形色色的路人…… 或许,他是在等待。等待那个仇人,有一天会不经意地,走进他的视野。或许,他只是习惯了这种观察者的身份。看透不说透,是最大的慈悲,也是最深的冷漠。 他端起茶碗,饮尽了那口苦涩的茶。 影 江南,烟雨朦胧。 一艘画舫,顺着碧绿的江水,缓缓而行。 十三娘坐在船头,换上了一身素雅的罗裙。她没有再戴面纱,任由江风吹拂着她的脸庞。她的脸上,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、恬淡的笑意。 她终于来到了她梦中的江南。她用酬金买下了这艘画舫,打算就这么沿江而下,看遍这江南的水,江南的桥,江南的人家。 她从袖中,取出一根银针,看了看,然后松开手。 银针落入江中,没有激起一丝涟漪,瞬间便消失不见。 从今以后,世上再无“影”。只有一个叫十三娘的女人,想在窗台上,养一盆最普通的、会开出紫色小花的车前草。 刃 那家深夜的羊汤馆,依旧开着。 瘸腿老板的身边,多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帮手。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高大的男人。 他不会算账,不会揽客。他只会劈柴,烧火,用一把巨大的砍刀,将一整只羊,干净利落地分解成最均匀的骨和肉。他的刀法,精准得像一门艺术。 是昆仑奴。 老卒走后,他便无处可去。他回到了那家羊汤馆,瘸腿老板收留了他。 他依旧沉默。但他不再是那把冰冷的、随时准备杀人的“刃”。食客们都喜欢这个不爱说话的大块头,因为他端上来的羊汤,总是最满、最烫的。 偶尔,他会站在门口,望着洛阳城里升腾起的万家灯火,黝黑的脸上,会露出一丝孩童般的、纯粹的茫然。 他或许永远也搞不懂那些复杂的“规矩”和“道义”,但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在这里,他不再是武器,只是一个靠力气换饭吃的普通人。 这就够了。 神都烟火如旧, 太阳照常升起。 东市的肉铺前,排起了长队。西市的酒肆里,胡姬们跳起了新的舞蹈。洛水之上,漕帮的船只来来往往,一个新的龙头,正在酒桌上和商人们推杯换盏。 南市的狗肉巷,一个新的小贼,正在觊觎某个富商的钱袋。 没有人记得那个叫老卒的副尉,没有人记得那个叫五郎的盗贼,更没有人知道,一场足以颠覆神都地下秩序的暗战,曾在这风雨中悄然开始,又悄然结束。 无数的阴谋与热血,无数的坚守与背叛,都像投入洛水的一颗石子,激起短暂的涟漪后,便沉入水底,再无踪迹。 只有这座城市,这座名为神都的巨大熔炉,依旧矗立。它冷眼旁观着一切,将所有的罪恶与理想,都碾碎、熔化,最终化为每日清晨,那袅袅升起的、千家万户的—— 烟火。 (全文 · 终) . _3 r- L7 Y& V4 s# c+ y0 G
8 e" r5 u4 Y7 s; a/ r( y) P. J) y2 i( i0 e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