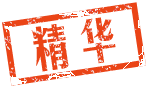9 w1 E! x1 z6 _$ G
第二则怪谈:《妆镜》
8 |: J7 D* s$ E8 g$ l
5 G! t- y1 s0 n1 R! y# J
. g$ Q# H) ?8 U* I0 C! h8 ?, [4 O0 s P+ B3 D# U
裴玄静的目光,穿过摇曳的烛火,落在了殿中一位女子的身上。那目光并非审视,更像是一条饥饿的蛇,在寻找猎物身上最柔软、最致命的要害。 “苏三娘,”他温润的声音在死寂的大殿中响起,带着一丝玩味的残忍,“你为求财而来,想必,你的故事,也与‘财富’有关吧?” 被点到名的女子,正是南市“奇货居”的东家,苏三娘。她是神都商界一株带刺的蔷薇,以美貌和手腕闻名。人们只知她富甲一方,却无人知晓她裙裾之下,掩盖着多少枯骨与沙砾。 她今日穿了一身石榴红的蹙金胡服,紧窄的袖口与腰身将她丰腴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,行走间,腰间的环佩叮当作响,如碎玉碰冰。她脸上画着精致的啼妆,眉心贴着一点嫣红的花钿,十指蔻丹鲜红如血。面对裴玄静的注视,她脸上恰到好处地浮现出一丝惊慌,那惊慌非但没有让她失色,反而像雨打的梨花,更添了几分楚楚动人之态。 然而,这一切的伪装,都逃不过谢云书那双受过特殊训练的眼睛。她清楚地看到,在苏三娘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深处,贪婪与不安正如同两条毒蛇,疯狂地纠缠、撕咬。她的美貌是她的武器,她的惊慌是她的面具。 “裴……裴先生说笑了。”苏三娘强作镇定,她缓缓站起身,婀娜的身姿在烛光下投射出摇曳的影子。她冲裴玄静妩媚一笑,那笑容足以让神都九成的男人为之失魂,但在这里,却像是投入深潭的石子,没能激起半点涟漪。“小女子不过是个本分商人,蝇营狗苟,勉强度日,哪有什么怪谈可讲。” “有没有,写个字便知。”裴玄静没有理会她的媚态,只是淡淡地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,指向那方散发着异香的古砚。 苏三娘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她的目光,不由自主地落在那方砚台上。墨香诡异,甜腻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朽气息,仿佛能直接钻入人的七窍,勾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与恐惧。她喉头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,握在袖中的手,指甲已深深掐入了掌心。她深知,踏入这座长修观,便等于签下了一纸看不见的契约,再没有回头的路。 她为何而来? 她为求财,也为求生。 神都的商海,远比西域的沙漠更凶险。近半年来,她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一片无形的流沙,无论如何挣扎,都在不断下沉。而更让她夜不能寐的,是那个藏在她妆台最深处的秘密,那个正一步步吞噬她魂魄的梦魇。听闻墨痕会之主裴玄静有通天彻地之能,能为人改运祈福,洞察鬼神之秘,她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,踏入了这片鬼蜮。 此刻,退无可退。 苏三娘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。她款款走到案前,那每一步都仿佛经过千百次的计算,摇曳生姿,仪态万方。她探出纤纤玉指,那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与漆黑的狼毫笔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她拈起毛笔,手腕悬空,沉吟片刻。为求财运,为照本心,也为……面对那即将吞噬自己的恐惧,她最终在雪白的宣纸上,写下了一个字。 镜。 她的字,与她的人截然不同。没有半分女子的娟秀柔媚,反而笔画锋利,结构开张,带着一股不加掩饰的精明与攻击性。尤其是“金”字旁的那一撇一捺,如出鞘的利刃,寒光四射。而右边的“竟”部,收笔处却微微颤抖,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墨点,如同一滴无法拭去的泪痕。 裴玄静凝视着那个“镜”字,嘴角的弧度愈发玩味,像是在欣赏一件等待宰割的艺术品。 “好一个‘镜’字。”他轻声赞叹,目光却冰冷如刀,“苏三娘,你可知,这镜,既能照人,亦能噬人。它能映出你的倾世容华,也能吞掉你的七情六欲。” 他开始了他的“墨痕溯源”,声音悠远,仿佛来自亘古。 “此字的隶书写法,‘金’旁宽扁,‘竟’部舒展,有容纳万物、照见真实之象。这是镜之本初,亦是你的‘前因’。你靠着一双比镜子更能洞察人心的眼睛,辨识奇珍,鉴别人心,才有了今日的家业。只是,你这双眼,看得透人心,却看不透自己。” 裴玄静的话,像一根冰冷的探针,精准地刺入了苏三娘记忆的最深处。那些被她用金银珠玉和胭脂水粉层层包裹、深埋心底的过往,瞬间被这股无形的力量强行挖开,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。 她并非生来就叫苏三娘,也并非生来就如此富贵。 她最初的名字,叫苏七娘。 她不记得父母的模样,只记得凉州城外,那片永远尘土飞扬的村镇,和永无止境的饥饿。她像一棵无人理睬的野草,在风沙与白眼中顽强地生长。为了活下去,她偷过路边食摊上滚烫的胡饼,为此被摊主打断过一根手指;她也曾因为半个被踩进泥里的铜板,和几条同样饥饿的野狗疯狂抢食,大腿上至今还留着狰狞的疤痕。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童年里,她比任何人、任何走兽都更早地明白一个道理:眼泪和祈祷换不来食物,只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颗够狠的心,才能让你活到明天。 她学会了看人。往来的商贩、兵痞、流民,她只需一眼,便能从对方的眼神、衣着和不经意的动作中,判断出谁是精明的狐狸,谁是肥硕的绵羊,谁又是披着羊皮的饿狼。她靠着这点天赋,为人跑腿,传递消息,用骗来的信任换取一点残羹冷炙。 转机发生在她十二岁那年。一位常年来往于丝绸之路的粟特老商人安翁,在他的商队里发现这个衣衫褴褛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眼神却亮得像狼崽子的小女孩。别的孩童见到他这高鼻深目的胡人,不是畏缩躲闪,便是麻木不仁。唯独这个苏七娘,敢直视他的眼睛,那眼神里没有乞求,只有冷静的评估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。 “小丫头,你不怕我?”安翁饶有兴致地问。 “怕你,你会给我吃的吗?”七娘反问,声音沙哑,却字字清晰。 安翁大笑,他从这个女孩身上,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他动了恻隐之心,更多的是一种发现璞玉的欣赏,便将她带在身边,让她在自己的商队里打杂。 安翁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光。这个看似精明的老胡商,却有着一颗罕见的、柔软的心。他教她识字,教她算盘,更将自己一生纵横商道的精髓,倾囊相授。 “七娘,”在一个星光璀璨的沙漠之夜,安翁指着跳动的篝火,对她说,“你看这火,它能给人温暖,也能烧毁一切。人心,比这火更难捉摸。做生意,最要紧的是什么?不是你手里的货物有多珍奇,而是你能不能看透买家的心。你要学会像最高明的猎人,看穿他内心最深的渴望,最怕的恐惧,最虚荣的念头。然后,你才能把任何东西,都卖给他。” 他还教她:“七娘,永远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底牌。你的钱,你的货,还有你的心,都要藏好了。在这条路上,最不值钱的,就是同情。” 那是她一生中最安稳、最充实的时光。她跟着安翁的驼队,穿越戈壁,翻越雪山,见识了拂菻国的玻璃、大食的香料、于阗的美玉。她的眼界与心胸,被这条流淌着黄金与鲜血的丝路无限拓宽。她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 然而,丝绸之路从不相信天长地久。 在一次翻越葱岭的途中,商队遭遇了早已埋伏好的马匪。那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。安翁为了保护那批价值连城的波斯香料,被乱刀砍死。临终前,他圆睁着双眼,用尽最后的力气,将一个沉甸甸的小皮袋塞进早已吓傻的七娘怀里,从喉咙里挤出几个被血沫堵住的字: “……活……活下去……孩子,记住……信金子……别信神佛……信自己的眼睛……别信……别人的心……” 那一刻,安翁眼中最后的光熄灭了。七娘心中的那束光,也随之熄灭。她抱着那袋滚烫的金币和安翁逐渐冰冷的尸体,在尸山血海中哭了一夜。第二天,她擦干眼泪,埋葬了安翁,然后背起那袋金币,独自一人,走向了东方。 她辗转来到了神都洛阳,这座天下最繁华,也最冷漠的城市。她为自己改名苏三娘,因为“三”这个数字,在《九章算术》里代表着“生万物”。她要在这座帝都,用安翁的血和自己的野心,生出属于她的万贯家财。 她用安翁教的本事,用自己那双洞察人心的天赋,在人头攒动的西市支起了一个小小的货摊。她将一枚普通的西域琉璃珠,辅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,编造出“人鱼的眼泪”的名头,成功地以百倍的价格,卖给了一位附庸风雅的富家公子;她将一块质地粗糙的和田玉璞,结合《山海经》的传说,描绘成“凤凰的遗卵”,高价出手给一位四处求医、求子心切的贵妇。 她的生意,就像滚雪球一样,越做越大。从一个小摊,到一个店铺,再到如今,南市最显眼位置,那座雕梁画栋、日进斗金的三层楼阁——“奇货居”。 苏三娘这个名字,也成了南市商人圈里,精明、财富与不好招惹的代名词。 安翁教了她如何看透人心,却没教她,当你看透了人心中的黑暗时,该如何自处。她选择的,是以更深的黑暗,去吞噬它。 一年前那趟远赴于阗的商旅,彻底改变了她的一切。 那是一段足以让最老练的行商都望而却步的旅程。为了获得一批独一无二的羊脂白玉,她的商队必须穿行一片被称为“白龙堆”的盐碱沙漠。白天,白花花的盐碱地反射着刺眼的日光,晃得人睁不开眼,仿佛行走在烧红的铁板上,连空气都带着灼人的热浪;夜晚,气温骤降,狂风呼啸,如万鬼哭嚎,刮在脸上像刀子割。向导说,这片死亡之海里有“盐碱魔”,会化作旅人心中最渴望的幻象——清泉、绿洲,或是家乡的亲人,将他们一步步引入死亡的陷阱。 苏三娘从不信鬼神,她只信自己手中的舆图和腰间的金币。与她同行的,还有另一支商队。领头的,是一个名叫马都尉的粟特商人。此人是她在洛阳商场上的老对手,为人阴险狡诈,多次在生意场上给她下过绊子,两人早已势同水火。此次不过是因路线相同,才暂时结伴,彼此都心怀鬼胎。 在进入白龙堆的第三天,两支商队都陷入了绝境。酷热加速了水分的蒸发,水囊比预想中更快地见了底。而下一个有淡水补给的绿洲,按照舆图,还有至少两天的路程。人心开始浮动,绝望像瘟疫一样,在驼铃声中悄然蔓延。马都尉的几个手下,已经因为脱水而出现了幻觉,指着远方的海市蜃楼,疯了般地尖叫。 然而,苏三娘并不慌张。这正是她为马都尉准备的坟场。 出发前,她早已用三倍的价钱,从一个曾被马都尉欺骗过的当地老牧民口中,买到了一份更为精确的手绘舆图。那上面,标记着一处被新月形沙丘掩盖的秘密地下泉。那是唯有最熟悉此地的牧民,才能在风沙变幻中找到的救命之地。 当晚,趁着马都尉的人因绝望而陷入混乱之际,苏三娘悄悄集结了自己的心腹。 “老板娘,我们真的要……”跟随她多年的老伙计阿贵,看着远处马都尉营地里微弱的火光,脸上满是犹豫和不忍。阿贵是她从西市的小摊贩时期就带在身边的,为人忠厚,是她身边唯一还存有几分“人心”的人。 苏三娘的眼神在夜色中冷如寒冰。“阿贵,你忘了安翁是怎么死的吗?在这条路上,不是他死,就是我亡。马都尉若是这次不死,等他回到洛阳,必定会想尽办法置我于死地。我们没有回头路。” 她的话,让阿贵打了个寒颤,再也不敢多言。 她带领自己的驼队,在夜幕的掩护下,悄然脱离了主路。在损失了两头因疲惫而倒下的骆驼后,她终于在一片连绵起伏的新月形沙丘背风处,找到了那个被枯死的胡杨根标记的救命泉眼。 泉水甘甜清冽,从沙地深处汩汩冒出。她的手下们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,疯了般地将头埋入水中牛饮。 苏三娘没有喝水,她只是用湿润的手帕擦了擦干裂的嘴唇,看着水面倒映出的自己那张被风沙侵蚀、写满疲惫与决绝的脸。安翁临终的话,再次清晰地在她耳边响起:“信金子,别信神佛;信自己的眼睛,别信别人的心。” 她心中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:回去告诉他们吧,救他们一命,日后在商场上或许还能留一线。但另一个更冰冷、更清晰、更诱人的声音却在低语:让他们死在这里。你不仅永远地少了一个最阴险的对手,还能在官府的文书记录下,名正言顺地接收他剩下的货物和商路。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。 仅仅迟疑了片刻,她便做出了选择。她转过身,对正在欢呼的伙计们冷冷地开口:“我们的水只够自己用,装满水囊,喂饱骆驼,休息两个时辰。天亮之前,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至于马都尉他们……他们的死活,自有他们的神佛保佑。” 那一刻,她清楚地看到了阿贵眼中一闪而过的震惊与恐惧。她知道,自己亲手斩断了心中最后一丝名为“温情”的牵绊。从今往后,她的世界里,只剩下冰冷的算计与得失。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那片死亡沙漠的边缘时,她遇到了一个形貌诡异的西域苦行僧。 那僧人赤足行走在滚烫的沙地上,身上只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赭色僧袍,形容枯槁,颧骨高耸,眼神却亮得惊人,仿佛两颗燃烧的炭火。他拦住了苏三娘的驼队,不为化缘,也不为乞食。 “女施主,你从死亡之地走出,心中却带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。”僧人缓缓开口,声音沙哑得像是被无数风沙磨砺过,“你用别人的死亡,换取了自己的新生,这笔买卖,看似划算,实则亏本。” 苏三娘心中一凛,面上却不动声色,警惕地握住了腰间防身的匕首:“大师何出此言?我听不懂。” “你懂的。”僧人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仿佛看穿了她的灵魂,“你的眼睛里,装满了黄金,也装满了恐惧。你害怕黑夜,害怕寂静,害怕你自己的影子。因为马都尉的亡魂,正跟在你的身后。” 苏三娘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僧人说得没错,自从离开那片沙漠,她夜夜被噩梦纠缠,总梦见马都尉那张因干渴而龟裂的脸,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她。 “大师……有何解法?”她几乎是脱口而出。 僧人摇了摇头,从破烂的僧袍里,捧出了一面古老的铜镜。 “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你的病,源于你的心,无药可解。”他将镜子递给苏三娘,“我见你与此镜有缘,便赠予你吧。此镜能映照人心所想,亦能成全人心所欲。但欲望的尽头,是更大的空虚,是更深的深渊。你好自为之。” 说完,他将镜子硬塞进苏三娘手中,然后转身便走,枯瘦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黄沙之中,仿佛从未出现过。 苏三娘低头看着手中的镜子。那是一面中土罕见的水银妆镜,入手冰凉,仿佛一块万年寒冰。镜背刻着繁复而诡异的花纹,似花非花,似兽非兽,盘旋交错,看久了竟让人头晕目眩。镜面光洁如水,却泛着一层幽幽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冷光,能将人的倒影照得纤毫毕现,连毛孔都清晰可见。 她当时只当是遇上了一个疯癫的胡僧,疑神疑鬼地将镜子丢进了货箱的最底层,很快便抛诸脑后。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,这面镜子,将成为她后半生所有辉煌与恐惧的源头。 裴玄静的手指,此刻正缓缓地移到了苏三娘刚刚写下的那个楷书“镜”字上。他的指尖并未触及纸面,却仿佛有一股寒气,从那字迹中透出。 “这便是你的‘现状’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,“你看,你写的‘镜’字,‘金’旁锋利外露,如刀似剑,充满了攻击性与掠夺之意。而右边的‘竟’部,却写得局促不安,上紧下松,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死死地困在里面,拼命挣扎,却又无法挣脱。三娘,你的财富,是靠着‘困住’了什么东西才得来的吧?是你困住了它们,还是……它们困住了你?” 苏三娘的脸色,瞬间由白转青。裴玄静的话,像一把生锈的钥匙,强行打开了她内心最黑暗、最不愿为人知的密室。 回到洛阳后,马都尉商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很快传来,官府的定论是“遭遇沙暴,不幸罹难”。苏三娘作为“幸存者”,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怀疑,反而因为“义助”马都尉家眷处理后事,在商界博得了一个“仁义”的好名声。她顺理成章地接收了马都尉大部分的商路和客户,奇货居的生意,一飞冲天。 然而,她很快就遇到了平生最大的劲敌——南市百年老字号“百宝斋”的少东家,钱宝峰。 钱家是洛阳的珠宝世家,根基深厚,人脉广博,从前朝起就为宫廷供应奇珍。钱宝峰更是个中好手,为人虽然傲慢,但眼光毒辣,手段老练。他视苏三娘这个靠着西域商路异军突起的“外来户”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认为她那些“讲故事”的卖货方式是旁门左道,玷污了珠宝生意的清誉。于是,他处处打压奇货居,明里暗里,使了无数绊子。 或是抢先一步截断她的货源,或是散布谣言说她的珠宝是以次充好,甚至买通地痞无赖,在她店门口寻衅滋事。苏三娘虽然一一化解,却也疲于奔命,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她知道,论财力,论人脉,论底蕴,她都远不是钱家的对手。长此以往,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,迟早会被钱宝峰蚕食殆尽。 就在她一筹莫展,甚至开始变卖部分家产以求周转之际,她无意中在整理库房时,翻出了那面被遗忘的西域古镜。 那晚,她坐在空无一人的妆台前,看着自己憔悴的容颜,愁眉不展。她随手拿起那面镜子,想看看自己究竟被逼到了何等狼狈的境地。 可当她望向镜中的瞬间,她愣住了。 镜中的那个自己,虽然容貌一模一样,但眉宇间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愁苦与疲惫,反而透着一股她所不具备的、运筹帷幄的沉静与冷酷。那双眼睛,深邃得像一口古井,仿佛早已看穿了所有的困局。 一个念头,毫无征兆地浮现在她脑海中:既然争不过货,何不毁了人? 这念头阴狠无比,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可不知为何,它又显得如此顺理成章,如此诱人。 那晚,镜子里的“她”,第一次对她“说话”了。并非发出声音,而是一种更直接、更无法抗拒的方式——将一个个精巧而恶毒的计策,如涓涓细流般,直接注入她的脑海。 “钱宝峰最大的弱点,不是他的生意,而是他的名声。他自诩为儒商,最重家族清誉。” “百宝斋每年都要向吏部侍郎宋大人府上送去厚礼,以求庇护。而宋侍郎,是出了名的清廉自守,最恨官商勾结之名。” “突破口,在宋侍郎那位刚刚从乡下接来的、愚蠢而又贪婪的侄子身上。” 在镜子的“指导”下,苏三娘设下了一个她自己都为之赞叹的连环毒计。 她先是让阿贵扮作落魄的西域商人,在宋侍郎的侄子宋衙内经常出入的酒楼里,“无意中”让他看到一块据说是从古墓中挖出的“血玉佩”。她深知宋衙内这种人的心理,越是得不到的,越是心痒。阿贵按照她的吩咐,先是故作神秘,拒不出售,吊足了对方的胃口。 几天后,她又安排了一场“英雄救美”的戏码。让宋衙内在街头“恰好”从几个地痞手中,救下了一位美貌的胡姬。而这位胡姬,正是她从平康里用重金请来的,最擅长逢场作戏的头牌。胡姬感恩戴德,对宋衙内投怀送抱。 在两人最情意绵绵的时候,胡姬“无意中”提及,自己有一位远方表兄,正是那位拥有血玉佩的西域商人。在胡姬的枕边风和宋衙内的软磨硬泡下,阿贵才“万般不舍”地,以一个高得离谱、却又在宋衙内承受范围内的价格,将“血玉佩”卖给了他。 而那所谓的“血玉佩”,不过是一块用特殊药水浸泡过的劣质玉石,不出一个月,血色便会褪尽,变成一块分文不值的石头。 拿到钱后,苏三娘立刻让阿贵带着那笔巨款,去钱宝峰的百宝斋,指名道姓要买最贵的一套南海珍珠头面。钱宝峰见有大主顾上门,自然是亲自接待,殷勤备至。阿贵付钱时,故意将钱袋里的银票“不小心”散落一地,那银票,正是宋衙内刚刚支付的、还带着宋府标记的官票。 这一切,都被苏三娘早已安排好的、混在客人中的几个“碎嘴婆”看在眼里。 不出三天,整个南市,乃至半个洛阳城,都在流传一个“有鼻子有眼”的谣言:百宝斋的钱少东家,为了打击对手,竟与吏部侍郎府的衙内勾结,设局做套,用一块假玉骗取暴利,再将赃款拿到自家店里“清洗”,简直是官商一体,无法无天! 谣言如风,很快就传到了御史台,更传到了那位爱惜羽毛胜过生命的宋侍郎耳中。 宋侍郎勃然大怒。他根本不屑于去查证事情的真伪,对他而言,这个侄子和那个商人的名声,已经玷污了自己的清誉。他盛怒之下,不仅将侄子打断腿送回了老家,更是立刻下令,彻查百宝斋历年来的账目。 墙倒众人推。钱宝峰平日里得罪的人本就不少,这一下,各种黑料被不断翻出。偷税漏税,以次充好,欺行霸市……短短半个月,百年老店百宝斋便被查封,家产充公。钱宝峰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泥潭,受不住打击,在狱中悬梁自尽。 此一役,苏三娘兵不血刃,就拔掉了自己最大的眼中钉。她趁机低价收购了百宝斋的部分产业,奇货居的声势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,再无人敢与其争锋。 胜利的当晚,她兴奋地拿出那面古镜,满心欢喜地看着镜中那个与自己一模一样,却又更美、更自信、更冷酷的影像,由衷地赞叹道:“我们……成功了!” 镜中的“她”也笑了,笑容完美无瑕,颠倒众生。可就在那笑容的背后,在镜子那片幽深无底的背景里,苏三娘清楚地看到了钱宝峰那张因绝望而扭曲、七窍流血的脸,一闪而逝。 “啊!”她吓得尖叫一声,手中的酒杯“哐当”一声摔在地上,碎成了千万片。 从那天起,她对镜子,由最初的利用,转为了深深的依赖,最终,化为了无边的恐惧。 镜中的“她”,不再是被动地提供计策,而是开始更频繁地、更主动地与她“对话”,教她更恶毒的商战手段,教她如何揣摩人心,如何利用人性中最卑劣的弱点。 “三娘,你不该对那个抵押祖宅的穷书生心软。他那块所谓的传家古玉是假的,就该让他倾家荡产,这才能让他记住教训,也是在警示后人。” “三娘,吏部尚书的夫人最是虚荣,你应该盛赞她的牡丹簪子独一无二,然后将那件仿得天衣无缝的赝品,以真品十倍的价格卖给她。她买的不是珠宝,是面子。” “三娘,你的伙计阿贵,对你太过忠心,也太过心软。这种人是绊脚石。是时候给他一笔钱,让他告老还乡了。我们的路上,不需要累赘。” 她一次又一次地按照镜子的指示行事,无往不利,财富像潮水般向她涌来。奇货居的楼阁越盖越高,她的名字在神都越来越响亮。但她的心,却越来越冷,人也越来越偏执多疑。 她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她觉得每一个伙计都在偷她的钱,每一个客人都想骗她的货。她最终还是听从了镜子的“建议”,在一个雪夜,给了忠心耿耿的阿贵一大笔钱,冷着脸让他离开了洛阳。她记得阿贵临走时,那张布满风霜的脸上,满是震惊和不解,他嘴唇翕动,最后只说了一句:“老板娘,你……保重。” 送走阿贵后,她遣散了所有老伙计,换上了一批她认为更“听话”、更没有感情的新人。她越来越孤僻,每天都要花上几个时辰,将自己锁在最深处的密室里,与镜中的“自己”对话。 她渐渐觉得,镜子里的那个,才是真正的、完美的苏三娘——果决、冷酷、美丽、永远不会犯错。而现实中的自己,不过是一具懦弱、多愁善感、会被无用情绪拖累的躯壳。 她开始在各种地方看到那些被她击败、吞噬的对手的幻影。 喝茶时,碧绿的茶汤里,会突然晃动出钱宝峰怨毒的眼睛;走在雨后的青石板路上,地面积水里会浮现出那个被她逼得跳井的绸缎庄老板苍白浮肿的脸;甚至在夜晚,风吹动窗边的芭蕉叶,那斑驳的影子,都像极了马都尉在沙漠中伸出的、干枯的手。 她惊恐地发现,这些人,他们的怨念,他们的魂魄,似乎都被吸进了镜子,成为了滋养镜中那个“完美苏三娘”的养料。镜中的“她”每吞噬一个灵魂,就变得更真实一分,更美丽一分。 她终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这面镜子,根本不是什么能实现愿望的宝物,而是一个以灵魂为食的魔物! 她想扔掉镜子。有一次,她下定决心,趁着夜色,将镜子用厚厚的布包起来,扔进了洛水。那一晚,她睡得前所未有的安稳。可第二天醒来,她发现那面镜子,正完好无损地摆在她的妆台上,镜面上还带着湿漉漉的水汽,仿佛在嘲笑她的不自量力。 从那以后,她再也不敢动扔掉镜子的念头。她甚至无法离开镜子超过一个时辰,否则就会心慌意乱,头痛欲裂,仿佛五脏六腑都被掏空,丢了魂魄一般。 她彻底沦为了镜子的奴隶。 她看着镜子,镜中的“她”也看着她,眼神里充满了她所熟悉的、那种混合着怜悯与嘲弄的神情。 “你在怕什么,三娘?”镜中“她”的声音,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在她脑海中响起,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、冰冷的温柔,“我们本就是一体。是我,让你摆脱了无用的情感,让你变得更强,更美,更富有。他们不是被你我害死的,他们是死于自己的愚蠢和贪婪。他们只是我们通往成功之路的垫脚石,他们的牺牲,是有价值的。” “不……你不是我!你是魔鬼!”苏三娘抱着头,惊恐地尖叫。 “我就是你,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渴望。”镜中“她”的声音依旧平静,“很快,我们就能彻底融为一体了。我会走出这方寸之地,去享受我们共同创造的这一切财富与荣光。而你,将会在里面,得到永恒的安宁,成为我永恒美丽的一部分,再也不用被这些肮脏的世事所烦扰。” 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?” 镜中“她”露出了一个诡异绝伦的微笑:“这不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吗?完美无瑕,不受任何情感的拖累。我们……交换吧。我来做外面的苏三娘,你来做里面的……倒影。” 苏三娘终于明白了,镜中的“她”,积蓄了足够的力量,准备与她交换位置! 这段时间,她夜夜噩梦,总梦见自己被困在一片冰冷光滑、无边无际的世界里。她能看到外面自己熟悉的房间,看到自己的妆台,自己的卧榻。而另一个“自己”,正坐在她的梳妆台前,用她的手,涂着她的胭脂,戴着她的珠钗,然后从镜子里,对自己露出一个胜利而又悲悯的微笑。 她快要疯了。 这才是她冒死前来墨痕会的真正原因。她要找一个能对付魔鬼的人,来救她的命! 裴玄静那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,如同一盆冰水,将她从恐怖至极的回忆中浇醒。 “至于这‘镜’字的‘未来’……”裴玄静提起另一支笔,在空中虚晃着,仿佛在描摹一个无形的字,“它的草书,会将‘金’与‘竟’连为一体,左右不分,真假难辨。如梦,如幻,如泡,如影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再也分不清谁是真人,谁是幻影。最终……归于一体,化为虚无。” 他放下笔,目光如炬,落在苏三娘那张因恐惧而扭曲、妆容都花了的脸上。他缓步向她走去,每一步都像踩在苏三娘的心跳上。他的手中,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巧的、擦得锃亮的铜制墨盒。 “苏三娘,你的故事很精彩。一个靠着吞噬他人而壮大,最终又被自己欲望的倒影所反噬的灵魂。虽然污浊不堪,却也……足够肥美。” 苏三娘惊恐地连连后退,却发现自己的双脚仿佛被钉在了地上,沉重如铁,动弹不得。她眼睁睁地看着裴玄静越走越近,那双温润的眸子里,此刻满是饕客即将享用美食的贪婪与陶醉。 她的目光,死死地钉在裴玄静手中那个小小的墨盒上。那擦得光可鉴人的盒盖,如同一面小小的、诡异的镜子。 她从那镜面倒映出的,不是自己的脸! 而是一张她无比熟悉,又无比恐惧的脸!那是一张美丽到毫无瑕疵,却又狰狞到令人作呕的脸!五官精致绝伦,皮肤光洁如玉,但那双眼睛里,却充满了无尽的怨毒、贪婪与疯狂! 那是镜中“她”的脸!它正在那小小的墨盒盖上,对着自己,露出一个胜利的、残忍的微笑! “不——!”苏三娘终于崩溃了,她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,那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绝望。 然而,裴玄静没有给她任何机会。他手腕一翻,那支早已蓄势待发的狼毫笔,已饱蘸着那诡异的墨汁,在宣纸上龙飞凤舞,迅速写下了一个诡异无比的草书“镜”字。那字迹纠缠盘旋,闪烁着妖异的金属光泽,仿佛一个正在缓缓旋转的黑色漩涡。 落笔的瞬间,苏三娘的惨叫声戛然而止。 她的身体,像是被投入水中的一幅水墨画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迅速变得模糊、扭曲。她华美的胡服,精致的妆容,丰腴的身体,都化作了一股带着五彩光华的烟气,仿佛孔雀的尾羽,又像是珠宝的光芒,被那个草书“镜”字所形成的黑色漩涡,一缕缕地、残忍地、鲸吞而入。 在被完全吸入的前一刹那,谢云书仿佛看到,那烟气中浮现出无数张脸:有安翁失望的脸,有马都尉干枯的脸,有钱宝峰怨毒的脸,有阿贵不解的脸……最后,所有的脸都融合成为了苏三娘自己那张充满惊恐与悔恨的脸。 她终究,还是被她自己一手造就的“镜”吞噬了。 片刻之后,一切恢复平静。 苏三娘消失得无影无踪,原地只剩下几件散落的环佩,在烛光下闪着冰冷的光。 而那张宣纸上,多了一个闪着诡异金属光泽、仿佛真的有一面破碎的镜子被嵌入了纸中的草书“镜”字。 裴玄静端详着自己的杰作,脸上露出心醉神迷的表情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张纸吹干,收入了那个特制的木匣之中。 殿内的气氛,已经凝固到了冰点。剩下的几个来看热闹的听众,脸色比死人还要难看。谢云书的心,也沉到了谷底。 她终于彻底明白,这个所谓的“墨痕会”,根本不是什么谈奇闻异事的雅集,而是一个狩猎灵魂、提炼罪孽的炼狱!裴玄静,就是那个手持画笔的阎罗! 下一个,会是谁? 裴玄静的目光,缓缓扫过最后一位新人,那个从始至终都像木偶般枯坐的年轻书生。 “李逸之,”裴玄静轻声道,声音里带着一丝异样的、仿佛是期待的温柔,“你的身上,有翰墨之香,也有……情爱之苦。那么,就请写下你的字吧。”
) K: R: i" C0 Q1 v$ t5 _1 f/ W) M0 O; j1 l! O( ?
' X( I6 c# A9 m7 r( t% V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