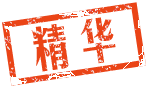# {( |$ M* m1 S
第二十九章 君子有远行
% X# V6 F' E( L
7 ?9 V) X' k, i/ R: n- G( D( t$ ]/ D$ P# X4 \
7 _$ ?/ c: |# j5 Q0 w又到了初秋的神都,依然是被桂子与菊香浸透了的。天高得像一块无瑕的蓝田玉,云是玉上随手勾出的几笔淡墨,风里带着一种干爽而清冽的气息,吹得人心都敞亮了几分。 南市依旧是那般的热闹,只是这热闹里,也添了几分秋日的丰足与从容。卖糖炒栗子的老汉,将那口大铁锅搅得“哗哗”作响,甜糯的香气能传出半条街去。果子铺前,石榴咧着嘴,露出玛瑙般的籽粒,柿子则被码得整整齐齐,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。 裴文远就站在街角一处茶楼的屋檐下,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 他今日穿了一身极普通的藏青色便服,头上未戴玉冠,只用一根竹簪束着发,身边也未带任何小厮。他刻意想融入这市井的人潮,可那份自幼浸润在骨子里的清贵之气,却让他依旧像一棵挺拔的修竹,卓然立于一片纷杂的灌木之间。 他的目光,穿过熙攘的人群,落在了斜对面那间小小的胡饼铺上。 铺子不大,却被收拾得窗明几净。赵七郎正赤着上身,浑身是汗地从那座粗犷的土馕坑里,用长长的火钳夹出一个个金黄酥脆的胡饼。他的动作充满了力量与节奏感,每一块肌肉都随着那揉面、贴饼的动作而贲张,脸上挂着一种发自内心的、毫无遮掩的满足。有熟客与他高声调笑,他便咧开嘴,露出一口白牙,回上几句响亮而憨直的话,引来一阵哄笑。 他的身后,孟月见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藕荷色布裙,腰间系着围兜。她没有在书案后读书,而是熟练地将烤好的胡饼用油麻纸一个个包好,递给排队的客人。她的动作依旧带着几分书卷气的优雅,却已然褪去了大家闺秀的生疏,多了一份融入烟火的娴熟与安然。 赵七郎忙碌的间隙,会习惯性地回过头。孟月见便会拿起挂在旁边的一只水囊递过去,再自然不过地伸出手,用一块干净的帕子,为他拭去额角和脖颈的汗珠。那动作,轻柔而专注,充满了不言而喻的亲昵。赵七郎仰头喝水,喉结滚动,目光却始终追随着她的身影,那眼神里的滚烫与珍视,是任何诗句都无法描摹的。 就在这时,一个五六岁的小童,举着刚到手的胡饼,兴奋地转身,却不慎被门槛绊了一下,一头栽倒在地。手中的胡饼,也飞了出去,在沾满尘土的地面上滚了两圈。 孩子的母亲发出一声惊呼,正要上前斥责,那孩子已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 排队的客人都停了下来,看向这边。 赵七郎却大笑着三两步跨过去,他没有先去扶那孩子,而是将那个沾满灰的胡饼捡了起来,吹了吹,对那哭得满脸通红的小童眨了眨眼:“没事没事,这饼,是咱爷们儿的战利品,待会儿拿去喂坊口的大黄狗!来,男子汉不哭,叔再给你一个刚出炉的,比这个还香!” 他不由分说地又从馕坑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饼,塞进孩子的手里。那孩子一手拿着新饼,一手抹着眼泪,竟忘了哭,呆呆地看着他。 孩子的母亲又窘又谢,连声说着要付钱。孟月见却已从铺里走了出来,她蹲下身,用帕子轻轻擦去孩子脸上的泪痕和灰尘,柔声对那妇人说:“嫂子莫要客气,孩子没摔着就好。这尘世奔波,谁还没个磕碰呢?” 她的话语温和,笑容亲切,瞬间便化解了那妇人的局促不安。她拉着妇人说了几句家常,又摸了摸孩子的头,那份从容与体贴,仿佛她天生就是这市井里的一员。 裴文远就站在那片阴影里,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 他看着赵七郎爽朗的笑,看着孟月见温柔的安抚,看着那对母子感激离去的背影。他忽然就明白了。 他曾以为,他与月见,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他有满腹才学,她有绝世风姿,他们在一起,会是一首格律工整、意象华美的绝句,会是一幅笔法精妙、意境高远的画卷,是神都城里人人称羡的“清风明月”。 可他今日才懂,他能给她的,是一座精心打理、完美无瑕的庭院,而她想要的,却是一片可以肆意奔跑、纵有泥泞的田野。他能与她谈论《诗经》中的“风雅颂”,却无法与她分享这一个胡饼里的“人情味”。 裴文远收回目光,转身离去。 走了几步,他忽然停下,靠在一棵老槐树上,闭上了眼睛。 他想起暴雨那夜,自己坐在书房里,听着管家的汇报。他确实派人去通报了河南府,也确实说了"以保全人身为要"。那是最理智的选择,最符合礼法的应对,也是他作为裴家公子,唯一"应该"做的事。 可当他第二日听说,那个卖胡饼的泥腿子,在泥水里泡了整整一夜,救出了孟家的雕版时,他忽然意识到—— 他输了。 不是输在才学,不是输在家世,而是输在,当那个女子需要有人为她涉险时,他选择了"理智",而那个粗人,选择了"去他娘的理智"。 他苦笑一声。原来,有些东西,是琴棋书画换不来的。 他所追求的“雅”,是一种需要刻意营造的精致。而她此刻所拥有的“烟火”,却是一种生机勃勃、粗糙而滚烫的真实。 前者是供人欣赏的画,后者是予人温暖的家。 他输了。输给的,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种人生。 裴文远站了许久,直到夕阳西下,将南市的街巷都染上一层温暖的金色。他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极淡的、温润的笑意,那笑意里,有怅然,有释怀,最终,都化作了坦荡。 他没有上前,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那间在暮色中亮起灯火的小小铺子,然后转身,将背影留给了那片不属于他的烟火人间。
* w% _' G, x1 ^2 F
' o% N8 x9 ]3 ?" A9 v/ a2 m& y, w数日后,一辆朴素的青篷马车停在了孟府门前。裴家的管事亲自将一个紫檀木盒与一封信,恭敬地交到了孟知俭的手中。 孟知俭在书房中打开了木盒。盒内铺着明黄色的锦缎,静静地躺着一对通体洁白、毫无瑕疵的和田玉如意。玉质温润,雕工精湛,在窗外透入的秋光下,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。这礼物,贵重、雅致,却也带着一丝玉石般的清冷与距离感。 他摩挲着那对玉如意,久久不语,随即唤来了孟月见。 孟月见接过那封信,信封上是她熟悉的、俊逸潇洒的字迹。她拆开信,在父亲沉静的注视下,轻声读了出来。 信的开头,是礼数周全的问候。继而,他以友人的口吻,坦然恭贺她与赵七郎喜结连理,言辞间毫无芥蒂,只有诚挚的祝福。信的末尾,他写道: “文远不日将离京,赴江南一带游学,访古探幽,或三五年,或七八载,归期未定。昔日种种,如梦如幻,幸得一识,已是三生之幸。” “神都风月,典赡文章,华美绮丽;终不及二位炉边烟火,一饭一蔬之暖。此去一别,山高水长,愿君与佳婿琴瑟和鸣,岁岁安康。文远再拜。” 读到最后一句,孟月见的声音微微有些停顿。她抬起头,看向自己的父亲。 孟知俭长长地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那一声叹息里,有惋惜,有感慨,但更多的,是一种彻底的释然。他知道,裴文远用这封信,这对玉如意,为所有人的过去,画上了一个无可挑剔的、君子般的句号。这无关胜负,只关乎选择。 孟月见将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。她没有将其放入收藏少女心事的梳妆匣中,而是走到书案前,打开了一个存放着家族重要书信的旧木箱,郑重地将它放了进去。 它属于她的过往,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历史,但也仅此而已。 她走到窗边,望向南市的方向。暮色四合,那里的万家灯火,正一盏接着一盏地亮起,其中,有一盏最温暖的灯,是为她而留。 从此,神都的清风与明月,各归其道,各自安好。 - Q7 t1 X5 p0 W9 N, y" s2 e, r
0 \# S! g* q6 N( q, O3 D' s2 l. \! o, r
9 X+ _' [" T. }6 r0 T
: u9 E0 k* }' K6 `6 e; ~第三十章 风雪夜% {" m. w: z& F
: ]8 n7 ?. J! w! Y
6 z: L0 z; s$ j$ S9 d/ }
7 G% u0 ]' W/ c* F& C' D腊月二十八了,距离过年只剩两日。 赵七郎正在后院劈柴,准备过节包饺子用。孟月见则在屋里,将《人间共此味》的五十册书,一本本用油纸包好,准备明日分送给"故事之墙"上的有缘人。 小院里,炉火正旺,雪落无声。 忽然,院门被粗暴地撞开。 一队府兵,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,为首的校尉,面无表情地出示了一块河南府的令牌。 "赵七,孟氏,有人告你们私印书籍,妄议朝政,煽动人心。随我们走一趟!" 赵七郎的斧子"当啷"一声掉在地上。 孟月见从屋里冲出来,脸色煞白:"你们是不是搞错了?我们只是编了本市井见闻,何来妄议朝政?" "是不是搞错,到府里再说!"校尉冷笑,"搜!" 府兵们涌进屋里,将那五十本《人间共此味》,连同孟月见的手稿、笔记,全部抄走。 陈大牛听到动静,赶来想要阻拦,却被一个府兵一脚踹倒在雪地里。拴住想冲上去,被赵七郎一把拉住。 "别动。"赵七郎压低声音,眼神示意他冷静。 他知道,在神都,与官府硬碰硬,只会死得更快。 孟月见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她强撑着镇定,对赵七郎使了个眼色:莫要反抗,我自有办法。 两人被押上囚车,在街坊们惊恐的目光中,消失在风雪里。
& ]# a) M7 W3 {* e; t# Z
4 @& ~. R- x$ i& `3 K8 \, D河南府的大牢,阴冷潮湿。 赵七郎和孟月见被分开关押。整整一夜,没有审讯,没有水米,只有无尽的等待和煎熬。 赵七郎坐在湿冷的稻草上,脑中飞速运转。 他想不通,那本书,他们只印了五十册,只送不卖,没有流通,怎么会被人告发? 除非…… 除非,有人一直在盯着他们。 他想起了最近常在饼铺附近徘徊的那几个陌生人,想起了金香园的钱半城曾放过的狠话,想起了这神都城里,那股无处不在的、令人窒息的告密之风。 他不怕死。在鹰嘴崖,他早就把命丢过一次了。 可他怕月见受苦。 她是大家闺秀,是孟博士的掌上明珠,如今却因为他,要在这冰冷的牢房里,承受这般屈辱…… 他狠狠锤了一拳墙壁,指节渗出血来。
: s. D+ P! X( D; l! h
0 {8 G. \4 _, E9 u* g% S5 [
次日辰时,审讯开始。 主审的,是一位刚从京城调来的推官,姓韩,人称"韩铁面",以严苛不讲情面著称。 大堂之上,威严森然。 赵七郎和孟月见被押了上来。两人都是一夜未眠,神情疲惫,但腰杆,却都挺得笔直。 "你们可认罪?"韩推官冷冷道,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 "不知所犯何罪。"赵七郎硬着脖子道。 韩推官冷笑一声,从旁边的案几上,拿起一本《人间共此味》,随手翻开一页,开始念: "'锦绣阁钱氏,以次充好,坑蒙良善,官商勾结,鱼肉乡里……'你们可敢说,这不是在影射朝中某些官员,与奸商沆瀣一气?" 孟月见抬起头,声音虽弱,却清晰:"回大人,此文所记,皆是实事。钱氏坑害陈氏一家,街坊皆知。我们只是如实记录,何来'影射'?" "好一个如实记录!"韩推官拍案,"那这一篇呢——'告密之风起,邻里相疑,人人自危……'你们这是在说什么?是在说朝廷鼓励告奸纳忠,反而害得百姓不安?这不是诽谤朝政,是什么?" "我们没有诽谤。"赵七郎沉声道,"我们只是……记下了我们看到的真实。" "真实?"韩推官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,"你一个贱民,一个妇人,也配谈'真实'?朝廷有朝廷的律法,你们私自编书,流传此等不当言论,就是扰乱民心!来人,先杖责二十,再押入大牢,听候发落!" 衙役们应声上前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—— "且慢!" 门外,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响起。 韩推官皱眉:"何人喧哗公堂?" 话音未落,孟知儉拄着拐杖,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 他身后,竟还跟着七八位白发苍苍的老者——有国子监的博士,有前朝的老臣,甚至还有一位,是当朝的太常寺卿。 "孟博士?"韩推官一愣,连忙起身拱手,"诸位大人,这是……" "韩大人,下官冒昧。"孟知儉不卑不亢道,"听闻韩大人要审小女与小婿,下官心中不安,特请几位老友,前来旁听。不知……可否?" 韩推官的脸色,有些难看。 他知道,孟知儉虽已致仕,但在神都文人圈子里,德高望重。他身后那几位,更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 "自然可以。"他皮笑肉不笑地道,"不过,律法无情,即便是孟博士的女儿,若真有罪,下官也不敢徇私。" "下官明白。"孟知儉颔首,"只是,下官有一言,不知当讲不当讲。" "孟博士请讲。" 孟知儉走到堂中,拿起那本《人间共此味》,翻开其中一页。 "韩大人适才所引'锦绣阁'一篇,下官细读过。此文所记,确系实事。钱半城坑害良善,街坊皆知,河南府亦有案底可查。我这女儿女婿,不过是将此事记录下来,以警示后人,何来'影射'之说?" 他顿了顿,又道:"至于那篇'告密之风',下官倒觉得,此文恰恰体现了圣上的英明。" "哦?"韩推官一愣,"此话怎讲?" "圣上鼓励臣民检举不法,是为了肃清吏治,维护律法。此乃圣君之举。"孟知儉朗声道,"但凡事过犹不及,若有宵小之徒,借'告密'之名,行诬陷之实,反而会让圣上的美意,被人利用。这本书里,记录的正是这种担忧——担心好的制度,被坏人用坏了。这难道不正是对圣上的忠心吗?" 这番话,说得极其巧妙。 既肯定了朝廷的政策,又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弊端,还把赵七郎他们的"记录",拔高到了"忠君"的层面。 韩推官哑口无言。 这时,人群中一位白发老臣站了出来,正是太常寺卿李大人。 "韩推官,老夫也有一言。"李大人捋着胡须道,"老夫读过此书,通篇所记,不过是市井小民的酸甜苦辣,人情冷暖。若连这都要定罪,那史官所修的《起居注》,岂不是篇篇都是'妄议'?" "圣人云:'民为贵,社稷次之。'"国子监的博士也开口了,"若连百姓的疾苦都不许记,连市井的真实都不许言,那我等读书人,所学的'以民为本',又算什么?" 一时间,诸位老臣纷纷发声,言辞恳切,却又句句在理。 韩推官的脸色,青一阵白一阵。 他心里清楚,这案子,是有人在背后推动,想借他的手,除掉赵七郎这个"眼中钉"。但他没想到,孟家的能量如此之大,竟能在一夜之间,请动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。 他权衡再三,终于开口:"诸位大人所言极是。此案,确实还需详查。今日……先行释放,容后再议。" 赵七郎和孟月见,终于可以离开这冰冷的公堂了。 , ~" x+ U3 W( a8 t" l; u. M9 t
# g5 H, K. O3 J+ A! e$ z走出河南府,已是黄昏。 雪,又下了起来,比昨夜更大。 街上的行人,都在匆匆赶路,准备回家过年。 孟月见转过身,对着孟知儉和诸位老者,深深一拜:"月见多谢父亲,多谢诸位伯父大人。" 赵七郎也郑重地跪了下去:"赵七无以为报,今后诸位但有所需,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。" 孟知儉扶起他们,长叹一声:"起来吧。这一关虽然过了,但往后,仍需小心。那幕后之人,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" "父亲,那本书……"孟月见有些不舍。 "书,他们已经扣下了。"孟知儉摇摇头,"但人,比书重要。" 李大人拍了拍赵七郎的肩膀:"小伙子,你做的事,老夫看在眼里。这神都城,需要你这样的人。只是,有些话,写在心里就好,不必都写在纸上。明白吗?" 赵七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 诸位老者,陆续离去。 孟知儉也要回府了,临行前,他看着女儿女婿,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 "爹……"孟月见唤了一声。 "好好过日子吧。"孟知儉说完,转身离去,背影在风雪中,渐行渐远。 赵七郎牵起孟月见的手。 两人站在风雪中,相视一笑。 他们知道,这一劫,只是暂时躲过。那本书,或许永远也无法流传于世了。 但他们也知道,只要他们还在,只要"故事之墙"还在,只要那炉火还在燃烧,这人间的温暖,就不会熄灭。 8 S& ~. S# _' }1 p
. j4 R( l4 z* J
终章 神都灯火
4 B9 L4 h5 D$ V$ y6 S/ X0 f/ U5 T
( w/ g: l4 x1 Y- X! D
6 z' q1 O1 k. G' L# \+ C: p5 n
& V9 `& P+ X! c: _# h) N0 X秋去冬来,每一年的冬至都如约而至。 这一年的冬至,神都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。街谈巷议间,人们都说,圣人登基已有十载,这洛阳城,也愈发繁华了。那雪,初时细如盐粒,悄无声息,只在坊间的青石板路上洇开一圈圈深色的湿痕。渐渐地,雪片变得丰盈,如千万只白蝶,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婆娑起舞,将巍峨的宫阙、森然的坊墙、寻常百姓家的青瓦屋顶,都温柔地覆上了一层素净的白。 告密之风,如一把悬在神都上空的无形利剑,让这风雪中的雄城,平添了几分往年不曾有的凛冽。街谈巷议,需得压低了嗓门;邻里往来,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探寻与审度。空气中,似乎总有一道看不见的目光,在审视着每一个人的言行。 然而,生活的洪流,却从未因此而停滞。南市的“赵氏饼铺”今日没有开张,门上挂着一块写着“东家过节,歇业一日”的朴拙木牌。那面五彩斑斓的“故事之墙”,在风雪中轻轻摇曳,像是在诉说着这一年来,市井间那些未曾被寒意冰封的、细碎的温暖。 铺子后院的小屋里,炉火烧得正旺,将一室都映得暖意融融,把窗外的风雪与寒气,都隔绝开来。 赵七郎和孟月见正围坐在桌边。桌上,摆着一盘新出炉的胡饼,正是那款纪念着他们第一次磨合的“风雪和鸣饼”,咸香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回甘。 在桌子的另一边,摊着一本刚刚发还回来的书。书是用最寻常的深蓝色布面做封,没有烫金,没有云纹,只用素雅的白线装订。封面上,是孟月见亲笔题写的五个风骨秀逸的大字——《人间共此味》。 这便是他们的心血。赵七郎用他那双善于与人结交的眼睛,去寻觅;孟月见则用她那支饱含深情的笔,去记录。从安仁坊刘婆婆那碗藏着思念的“宫灯汤圆”,到国子监张生那方匿名的“高义墨锭”,再到绣娘王婆婆那根被重新拾起的“尊严丝线”……他们记下的,不是奇闻,而是人心。 “成了。”赵七郎伸出他那双依旧粗糙、却温暖厚实的大手,小心翼翼地抚过封面,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。他的眼中,是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自豪。 孟月见含笑看着他,为他斟上一杯温热的黄酒。可她的眼底,却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。 “七郎,”她轻声说,“这本书,发还了的五十册,都按你的意思,赠给了‘故事之墙’上有缘的那些人。只是……我这心里,总有些不安。” 赵七郎端起酒碗,不解地看着她:“这有何不安?这是好事啊!” “你久在边塞,不晓得如今神都的风声。”孟月见的声音压得更低了,“如今这世道,言语是蜜,也是刀。我们这书,记的虽是寻常百姓,可‘记言’、‘流传’,都是忌讳。我怕……怕有心人再拿去做文章,给你我招来无妄之灾。” 赵七郎沉默了。他想起之前的风波…… 他放下酒碗,伸手将妻子微凉的手掌握进掌心。他没有说些“别怕”、“有我”之类的空话,只是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。他的掌心,有常年揉面留下的厚茧,和炉火赋予的滚烫温度。 “月见,”他看着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道,“在边关,越是怕,刀就得握得越稳。在神都,也是一个理。越是风大,咱们这炉火,就得烧得越旺。若人人都因害怕而不敢说话,不敢记下身边的好,那这世道,才真是要冻成冰坨子了。” 孟月见怔怔地看着他。这个男人,不通经史,不懂格律,却总能用最朴实的言语,说出最通透的道理。那份从血与火中淬炼出的、坦荡无畏的勇气,瞬间便驱散了她心中的所有阴霾。 是啊,她想。她所嫁的,本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丈夫。她所爱的,也正是这人间烟火里,不屈不灭的一点真心。 “好。”她反手握住他的手,眉眼弯弯地笑了,如一轮新月,照亮了这风雪中的陋室,“那咱们就……把这炉火烧得再旺些!” 窗外,雪越下越大。屋内,炉火哔剥作响。 赵七郎为孟月见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,汤色奶白,是他记忆里边塞的味道。孟月见则为他夹了一块自己新做的、精致玲珑的“百合如意糕”,糕点清甜,是她书卷里江南的雅致。 他大口喝汤,辣得额头冒汗,直呼痛快。她细细品糕,甜得眉眼舒展,满心安宁。一刚一柔,一咸一甜,在这小小的桌上,调和成一种独一无二、只属于他们的滋味。 “说起来,”赵七郎忽然想起什么,憨笑道,“当初裴公子送你的那对玉如意,还在吗?” “在的。”孟月见答,“收在箱子里呢。怎么了?” “没怎么,”赵七郎嘿嘿一笑,指了指她盘中的糕点,“就是觉得,他那玉做的如意,好看是好看,但终究是冷的、硬的。还是你这糯米做的如意好,能吃,还暖心。” 孟月见被他这番歪理逗得忍俊不禁,嗔怪地白了他一眼,眼波流转间,皆是化不开的柔情。 饭后,两人并肩立于窗前。 夜幕早已降临,雪势却未停歇。整个神都,都被笼罩在一片静谧的、梦幻般的雪白之中。远处,万家灯火,一盏接着一盏地亮起,在漫天风雪里,晕开一团团温暖而朦胧的光晕。每一盏灯火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,一段故事,一捧正在升腾的、对抗着世间寒冷的烟火。 赵七郎伸出手臂,将孟月见轻轻揽入怀中。她自然地将头,靠在他宽厚而坚实的肩上。 “月见,你看。”他轻声说,呼出的白气,在窗上凝成一团薄雾,“这神都,就像一个大大的胡饼,咱们俩,就是这饼上的一粒芝麻。” 孟月见没有说话,只是将他的手臂抱得更紧了些。她知道,他们这粒“芝麻”,与别的芝麻,已然有了不同。 他们不仅仅是这万千烟火中的一粟,更是这烟火的守望者。 他们用一双脚,去丈量市井的温度;用一双手,去揉捏生活的本味;用一颗心,去倾听无名的故事;用一本书,去对抗遗忘与冰冷。 这守望,无关功名,无关对错。它只是两个曾被命运磨砺过的人,在找到彼此之后,选择用自己的方式,为这片他们深爱的人间,留住那一点最可贵的、名为“人情”的暖意。 雪,还在静静地、静静地落下。 那间小小的饼铺,与这神都的万家灯火,一同亮着。它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,守望着这座伟大都城里,每一个平凡而坚韧的灵魂,和他们那些值得被永远铭记的、独一无二的人间滋味。 - V6 _! X4 T9 `2 q/ T9 X* |. a
人活一世,漂泊也好,富贵也罢,所求的,不过就是这么一口能暖到心窝里的热乎气儿。 (全书完) 6 S K! O9 P' n1 X/ q% k M/ D7 y
. B6 f3 s' }3 O1 H
( o& \% x( X- V+ l- O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