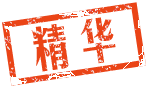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-10-19 10:31 编辑 3 k! _* }/ o1 n0 G! s
2 G# l' @' A+ s1 c第三幕:债务的流沙
+ l0 b% h9 q; J- w* z, Q4 U
" L6 S' I" P* U- n第九章:金丝雀0 {& _1 p6 Y- d
! }' E' o& q% M( k( o1 ]8 u7 J( d* T/ S- t
7 W. Z$ h4 p/ k4 `7 ^自打成了崔夫人的专属信使,阿郎的日子便过得像一首被精心谱写的曲子,每一个音符都精准、体面,却也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情。 天光未亮,鸡鸣三遍,南市的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混沌的梦乡里,阿郎的院子已经亮起了灯。他不再像过去那般,被潮湿的霉味和邻居的咳嗽声唤醒。如今叫醒他的,是刻在骨子里的焦虑。他睡得极浅,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惊坐而起,侧耳倾听鸽舍的动静,生怕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疙瘩出了半分差池。 他的新家在南市最靠近洛水的一隅,一处独立的二进小院。青砖铺地,院角植着一株芭蕉,雨打其上,别有几分雅致。这雅致,是他用崔夫人赏赐的银铤换来的,每月光是租金,就足以让一个寻常南市家庭过上一年。他为鸽子们搭的鸽舍,用的是上好的杉木,通风向阳,比他自己住的卧房还要讲究。食槽里永远盛着饱满的火麻仁和豌豆,水罐里是取自洛水的清冽活水。 他自己也换上了细麻裁成的圆领袍,腰间束着革带,脚踩一双干净的千层底布鞋。走在南市的街上,从前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泼皮无赖,如今见了面,都会远远地堆起笑脸,喊一声“郎君”。 他每日清晨,会先仔细检查每一只鸽子。他如今的鸽群,已经从最初的两只,扩充到了二十余只。每一只都羽翼丰满,眼神锐利。他会挑出状态最好的几只,放飞进行晨训。看着它们化作白点,消失在洛南方向的天际,阿郎心中会涌起一种短暂的、近乎虚幻的自豪感。 而后,他会仔地形理自己的仪容,直到镜中的自己看起来与“洛南”二字相称,才锁门离去。 渡过洛水,便是另一个世界。浣溪沙的侧门总是为他准时开启,开门的仆役,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,既不亲近,也不疏远。他从不多言,只是微微颔首,接过侍女晚晴递来的信筒。晚晴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,但眼神总像隔着一层薄雾,你看得见她,却永远看不透她。 “阿郎,今日这封信,务必在一个时辰内,送到开化坊的‘听雪楼’。”晚晴的声音,也如她的眼神一般,轻柔,却毫无温度。 “明白。”阿郎的回答永远简短有力。 他接过信筒,能感觉到上面还残留着崔夫人指尖的余温和淡淡的熏香。这曾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荣幸,如今却只觉得那是一块温热的烙铁。他将信筒缚在“云”的脚上,放飞。白鸽冲天而去,他则会寻一处僻静之地,静静等待。 他从不离开洛南。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封信何时会来。他就像一只被金线拴住的雀鸟,活动范围仅限于主人的庭院内外。他可以在洛南的茶馆里坐下,点一壶价格不菲的蒙顶甘露,听着周围的雅士们谈论着他听不懂的诗词歌赋和朝堂秘闻。那些人衣着华贵,举止从容,看他的眼神,偶尔会掠过一丝好奇,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声的审视,像是在打量一件新奇的摆设。 他与他们之间,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。他能闻到他们身上昂贵的香料味,却闻不到他们言语中的真意。他能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,却看不到笑容背后的算计。 午后,他会收到第二封、第三封信。送往不同的地方,给不同的人。有时,他会收到一笔丰厚的赏钱,几枚沉甸甸的银铤,或是几贯崭新的开元通宝。他会小心翼翼地将钱收好,心中盘算的却是这个月高昂的开销:院子的租金、鸽粮的费用、打点浣溪沙门房仆役的“茶水钱”,还有……寄回老家给多病母亲的汤药费。 是的,他在南市,还有一个家。一个他如今很少回去,却必须用钱供养的家。母亲的信,总是那几句:“吾儿在外,万事小心,勿念家中。”可信中夹带的,却是越来越长的药方。 洛南的奢华,与南市的拮据,像两块巨大的磨盘,日夜碾磨着他的神经。他挣得越多,花得也越多。他像一个筛子,无论多少钱流进来,都会从无数个孔洞中流出去。他必须维持在洛南的体面,才能继续挣这份钱;而维持这份体面,又让他几乎没有分毫盈余。 日落时分,他会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南市的小院。南市的喧嚣和烟火气,在此时不再让他感到厌恶,反而有一种不真实的亲切感。他会亲手为鸽子们清洗鸽舍,添加食水,检查它们的身体。只有在触摸到鸽子温热的身体,感受到它们轻微的脉搏时,阿郎才能感到一丝真实。 辛夷来过一次。 她提着一小袋自家磨的新米,站在院门口。看到院内的芭蕉和干净的青砖,她愣了许久。 “你这里……倒像个正经人家了。”她的话里,听不出是褒是贬。 阿郎正在擦拭一只青瓷水罐,闻言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 辛夷走近,看着他身上那件一尘不染的细麻袍子,又看了看他那双因常年握缰绳和训鸽而依旧粗糙的手,轻声说:“阿郎,你瘦了。也……老了。” 阿郎的动作一顿。他抬起头,从辛夷清澈的眼眸里,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。眼神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疲惫和警惕,像一只时刻防备着猎鹰的兔子。 “洛南的差事,很辛苦吧?”辛夷问。 “挣钱哪有不辛苦的。”阿郎避开了她的目光,淡淡地回答,“但干净。没有刘三爷,没有坊卒的刁难,一笔账一笔钱,清清楚楚。” 辛夷沉默了。她将米袋放在石桌上,说:“这是新碾的米,熬粥喝,养胃。看你脸色不好。” 她顿了顿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:“你自己……多保重吧。别飞得太高,忘了回家的路。” 辛夷走后,阿郎独自在院中站了很久。晚风吹过芭蕉叶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一声声无奈的叹息。他看着自己整洁的衣袍,看着这间雅致的院子,看着鸽舍里那些神俊的白鸽。他拥有的,是他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切。 可为什么,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华美笼子里的金丝雀?食无忧,居有处,每日梳理着光鲜的羽毛,唱着主人喜欢的调子。 却唯独,失去了自由。 夜深了,他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。南市的喧嚣早已沉寂,洛水的流水声隐约可闻。他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的,不是洛南的亭台楼阁,也不是崔夫人那张模糊而优雅的脸,而是辛夷那双充满担忧的眼睛,和她那句“别飞得太高,忘了回家的路”。 他猛地睁开眼,盯着黑暗中房梁的轮廓。 回家?他还能回得去吗? 一旦品尝过天空的滋味,又有哪只鸟儿,愿意再回到地面上的泥潭里去呢?哪怕,那片天空,只是一座更大、更华丽的囚笼。 ; Y( f. [* W% y* s7 e
4 Q3 z7 x9 V* {) N, F) ^9 @
第十章:夫人的夜行" ~9 M+ J- K: v% ^; R! z% _, w
8 ^& U4 D( _/ {" G0 G" D
阿郎以为,浣溪沙的生意,永远是那些风雅的诗笺和花帖。他错了。那些不过是崔夫人对他的试探,是包裹在毒药外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糖衣。当她确认这只“金丝雀”足够听话、足够可靠之后,真正的“差事”才开始显露其狰狞的面目。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,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水汽,连一丝风都没有。阿郎刚给鸽子们喂完水,准备歇下,浣溪沙的仆役却敲响了他的院门。这极不寻常,崔夫人的信,从未在深夜传来。 来人递给他一个黑色的布包,入手沉甸甸的,里面似乎是某种金属器物。 “夫人的吩咐,”仆役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严肃,“亥时三刻,将此物送到通济坊,赵国公府的后门。交给一个右眼角有颗痣的管事。记住,走小路,莫要引人注目。此事若成,夫人有重赏。” 没有信筒,没有鸽子。这是第一次,需要他亲自“跑一趟”。 阿郎的心,猛地一沉。他掂了掂手里的布包,那重量让他感到一阵心悸。这不是诗笺,更不是花帖。 “是什么东西?”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。 仆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:“不该问的,别问。你只管送到。夫人的事,你担待不起。” 说完,仆役便转身融入了夜色,留下阿郎一个人,手捧着那个仿佛会烫手的布包,站在院中。 他没有选择。他知道,从他踏入浣溪沙的那天起,他就没有了选择。拒绝,意味着失去一切,甚至可能招来更大的祸端。 他换上一身不起眼的深色短打,将布包紧紧地藏在怀里,如同揣着一块烧红的炭。他没有走南市的大街,而是钻进了那些平日里连乞丐都嫌弃的、黑暗泥泞的小巷。神都的夜晚,并非一片死寂。更夫的梆子声,酒楼里传出的隐约丝竹,巡夜金吾卫的甲叶摩擦声,交织成一张紧张而诡异的网。 每一步,他都走得小心翼翼。每一次转角,他都屏息凝神。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在暗夜里潜行的老鼠,而周围的黑暗中,有无数双猫的眼睛在盯着他。 通济坊是神都有名的权贵聚居之地,坊墙高大,守卫森严。赵国公府更是气派非凡,府邸的黑漆大门在夜色中如同一只沉默的巨兽。阿郎绕到后门,那是一扇不起眼的角门,隐在一条深巷的尽头。 他按照约定,轻轻叩击了三下。 门轴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,开了一道缝。一只灯笼从门缝里探出来,昏黄的光照亮了一张毫无表情的脸。那人右眼角,果然有一颗黑色的肉痣。 “东西。”那人的声音沙哑,像是喉咙里卡着一口老痰。 阿郎从怀中掏出布包,递了过去。 那管事接过布包,打开看了一眼。借着灯光,阿郎瞥见了里面的东西——那是一套精巧的银质酒具,一只酒壶,两只酒杯,在灯下闪烁着诡异的光。酒具的样式,他似乎在哪里见过。 管事没说什么,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,塞到阿郎手里,然后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 阿郎捏着那张纸,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他不敢久留,迅速转身,原路返回。一路上,他总觉得那套银酒具的形象在脑中挥之不去。 直到他快要回到自己的小院时,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他。 他想起来了!上个月,他在洛南的茶馆里,听邻桌的两个闲人谈论过一桩朝堂上的案子。御史台的一位姓张的监察御史,弹劾吏部的一位侍郎贪赃枉法。那位张御史,素以刚正不阿闻名,据说滴酒不沾,唯一的爱好,便是收藏一套前朝巧匠打造的“月影”银酒具。 阿郎的后背,瞬间被冷汗浸透。他明白了。崔夫人不是在雇佣他,而是在收买他,用一套他无法拒绝的房产,买下了他的沉默,也买下了他的良知。那套送去的银酒具,是栽赃的证物。他,亲手递出了这件毁灭一个清官名誉的“证物”。 他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揣着那份滚烫的地契,在深夜的南市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。他感觉自己肮脏不堪,需要一个地方躲藏。鬼使神差地,他走到了“半两食铺”门口。 铺子已经貌似打烊,门板只留了条缝,透出微弱的灯光。韦掌柜正在收拾,准备给晚归的客人们留一碗热汤。他看到门外脸色惨白的阿郎,愣了一下,什么也没问,只是默默打开门,给他盛了一碗热汤。 阿郎端着碗,手在发抖,却一口也喝不下去。汤的香气,这纯粹的、人间烟火的味道,此刻对他而言是一种审判。这股暖意,比任何责骂都让他难受。 他最终将碗放下,从怀里掏出几枚银钱——远超一碗汤的价格——放在桌上,沙哑地说了一句“对不住”,便仓皇逃离。他逃离的不是食铺,而是自己仅存的、被这碗热汤唤醒的良知。 回到院中,他瘫坐在冰冷的石阶上,夜风吹来,他却感觉不到一丝凉意。他只觉得浑身发冷,从骨髓里透出来的寒意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这双手,曾几何-时,只懂得抚摸鸽子的羽毛,如今,却沾染上了他看不见,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污秽。 辛夷的话,在他耳边反复回响:“洛南的脏,是藏在锦缎下的脓疮。一旦沾上,是会烂进骨头里的。” 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信使,一个旁观者。直到今夜,他才惊恐地发现,自己早已被织进了这张大网,成了一个递送毒药的帮凶。那张地契,不是赏赐,是投名状。 他看着鸽舍里那些在睡梦中发出咕咕声的白鸽,它们依旧那么纯洁,那么无辜。他伸出手,想要像往常一样去抚摸它们,手到半空,却又猛地缩了回来。 他觉得,自己的手,已经脏了。配不上它们了。 从这一夜起,阿郎的梦境,便不再有蓝天白云。取而代之的,是无尽的黑暗小巷,和那套在灯光下闪着诡异光芒的银质酒具。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房产,却永远地失去了一样东西——安稳的睡眠。 & X4 t0 ^- r- h
- Z! I! _3 E4 J
9 Y* a: ~* Z; [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