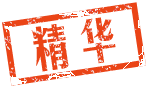TA的每日心情 | 开心
2020-4-8 10:45 |
|---|
签到天数: 227 天 [LV.7]分神
|
* u4 M& T6 d2 c7 `. \8 q: A
刘郎归不归?——唐诗论情之刘禹锡(上)
$ J/ g' V N* ]6 S" e
# f& {1 v& J9 h9 v' w- }2 \序章:命运的开场——前度刘郎7 x0 B! y! z4 G. w
公元815年的春天,长安城在一场盛大的喧嚣中醒来。十年前被帝国权力中心驱逐的诗人刘禹锡,回来了。
4 X3 {: F5 |3 F1 K8 U+ N8 n2 d7 g* `8 }8 Z
这不是一次荣归。长安的空气对他而言,熟悉又陌生,像一件早已不合身的旧袍子,裹着一个被岁月和苦难重新雕琢过的灵魂。那年他四十三岁,鬓角或许已染上了朗州(今湖南常德)蛮荒之地的风霜。十年,足以让一座帝都忘记一个人的名字,也足以让一个人看清一座帝都的凉薄。' ]) p2 P7 ?; Y
/ S4 t, I! L; X/ L此刻,他正走向玄都观。那不是一次寻常的踏春,而是一场无声的对峙。春风扬起的“紫陌红尘”,温柔地拂过他的脸颊,却像砂砾一样磨砺着他的内心。这尘土里,混合着新贵们的马蹄声、仕女们的欢笑声,以及权力的气味。整个长安都在谈论玄都观的桃花,仿佛那不是花,而是帝国最新的恩宠与时尚。
/ f) D; {" Q% n+ Q2 @
- N% ~$ j, O0 g4 e0 G) }$ b他穿过涌动的人潮,那些“看花诸君子”,一张张春风得意的脸,在他眼中不过是模糊的剪影。他们是十年间朝堂上新崛起的力量,是靠着他与同伴们政治革新失败后的废墟,才得以攀上高位的人。他们赏的不是花,是自己的权位和胜利。
* v6 \* L; o. H1 k! Z, E; o m, w* e0 b A; r$ C6 i- D) |
刘禹锡的呼吸或许有些沉重,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被埋葬的青春之上。十年前,他和柳宗元、王叔文等人,怀着利刃般的锐气,试图为这个积弊丛生的帝国刮骨疗毒。那场轰轰烈烈的“永贞革新”,如夏日惊雷,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晦暗的天空,却也迅速被盘根错节的宦官与藩镇势力扑灭。那一百四十六天的理想主义,最终换来了长达十年的流放。他被扔到遥远的朗州,一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,一个足以让任何人的雄心壮志都化为瘴气的地方。7 x' Y: S) q3 d
- U- N0 [4 N- D: X, v
现在,他回来了。站在玄都观前,他看到了那“千树桃花”。它们开得如此恣意、如此炫目,仿佛在向他炫耀一个没有他的长安是何等繁华。他能听到周围人的议论,能感受到那些投向他这个“前朝旧臣”的、夹杂着好奇与轻蔑的目光。4 I! E; [+ ~- y* U8 n# q
8 u6 \4 j, B8 b& g. w6 R0 V( _7 M
悲伤?愤怒?不,那都太平庸了。在刘禹锡的胸中,正升腾起一种更为复杂、更为锋利的情绪——那是极致的骄傲与极致的嘲弄混合而成的烈酒。
+ i8 O. b0 A# c$ C- C
/ e) N |4 o5 U W( O他一定是在某个瞬间停下了脚步,整个世界的喧嚣都退去了。他的眼中只有那些桃花,那些在他离去之后才被栽种、如今却被奉为奇观的桃树。一个念头,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他。他找到了一个词,一个动作,来定义这十年,来回应眼前这整个虚伪的盛景。, I8 I8 t' Q4 w1 C* e! ], J
8 p0 F. V% U5 L& k; T3 J% k O于是,他提笔写下了那首足以再次改变他命运的诗——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:9 s5 k6 b' O9 D3 M8 ?: [
3 A4 i2 I7 @+ {; K) G7 K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 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$ I V9 D+ y3 e$ H& f7 J* i5 [( W) @5 \5 ]7 x3 Y! H& ^
当他写下最后一个字,“栽”,那一刻,他不是在记录一个事实,而是在进行一次宣判。这个“栽”字,是他投向整个时代的一柄匕首。它轻描淡写,却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。他在说:你们引以为傲的这一切,不过是我离去之后才发生的小事。你们是后来者,是新贵,而我,刘禹锡,是历史本身。你们的根基,甚至都还没有我的放逐史来得长久。
2 p* m# X& Y: M( |: o
3 V3 s7 ?+ l. y( o' |3 Z& g* D2 D( Y这便是刘禹锡。他不是一个在命运的铁蹄下呻吟的懦夫,而是一个敢于用诗句直面命运、甚至反唇相讥的斗士。他的情感,从不由他人定义,他的悲伤,总能淬炼出最坚硬的骨头。
6 S) O9 h; o1 C6 a: v: y
+ m$ Q( r, c/ N/ X现在,让我们潜入刘禹锡的世界,去看一个被誉为“诗豪”的男人,如何在长安的迷梦中锻造利刃,如何在巴山楚水的泪痕中淬炼灵魂,又如何在东都洛阳的晚霞中,寻得最终的安宁与不朽。
9 W5 {6 X2 t: q4 j: {5 i# e) P8 r: K e( w$ E3 Z
这,是一个关于爱、痛、痴与怨的故事,是一个关于一颗伟大的心脏如何搏动的故事。1 Y' l! m/ @! \) @: O
. M8 F6 J- L; Y% K7 w& s: N第一幕:长安之梦——利刃与朝露 (793-805)
( {% t |, T4 o1 |1 G \+ Z( i4 b, Z/ G" V
幕布拉开: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
1 T2 {* C' L# ~4 W0 q5 o6 w: w! E# \9 X; ^2 g0 Q( H7 }& b
中唐的长安,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华美宫殿。安史之乱的创伤犹在,帝国的肌体上长出了两个致命的肿瘤:内有宦官专权,外有藩镇割据。宦官们掌握着京城的精锐部队神策军,甚至可以废立皇帝,权势熏天;地方的节度使拥兵自重,视朝廷号令如无物,俨然一个个国中之国。这是一个英雄无力、理想显得尤为脆弱的时代。* u! j, w7 k7 J# X. z% j
* J- D2 x( f) y# j' Z就在这样的氛围中,两个年轻人走进了长安。公元793年,二十二岁的刘禹锡与二十一岁的柳宗元,同一年进士及第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初次相见时的情景。或许是在雁塔题名之后,长安的酒楼上,两个同样才华横溢、同样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,一见如故。刘禹锡,或许带着江南水乡的灵秀与北地士族的傲骨,言谈间锋芒毕露;而柳宗元,出身世家,气质更为沉郁,但目光中同样燃烧着改变世界的火焰。他们的相遇,不是偶然,是那个时代仅存的一点理想之光,在寻找彼此的映照。5 `+ |- O* W; I- M6 F6 q; z7 C
5 _8 h) [2 _5 W
这份友谊的真正淬炼,发生在他们共同担任监察御史之时。御史台,是帝国的眼睛和耳朵,本应是激浊扬清之地。然而,他们看到的却是盘根错节的腐败和令人窒息的黑暗。每一次弹劾,都可能撞上宦官或权臣筑起的高墙;每一次调查,都让他们更深地触摸到帝国衰败的脉搏。这共同的经历,让他们的友谊超越了诗酒唱和,升华为一种坚实的“革命情谊”。他们不再是旁观者,他们决心成为棋手,要亲自扭转这盘必输的棋局。
1 n8 H1 |1 e" V* A, z! q
. E$ D0 X( _* s; [6 E/ q他们找到了那个能让他们放手一搏的人——太子侍读王叔文。王叔文是当时太子李诵身边最受信任的智囊,一个同样渴望改革的政治人物。于是,一个以王叔文为核心,以刘禹锡、柳宗元等青年才俊为骨干的政治团体悄然形成。他们在等待,等待一个机会,等待太子登基的那一天,用他们手中那柄磨砺已久的利刃,划破笼罩大唐的阴霾。0 F3 b! h& l7 N
7 @ y8 S' p, f# I) b7 [" t2 k那时的他们,就如清晨的朝露,晶莹剔透,却也预示着在日出之后,必将蒸发消散的命运。; a4 n3 v( r. G( a4 O0 R
$ d$ \9 ~/ e2 b$ m& Q永贞革新:一百四十六天的烈火与幻梦- i; ~: m1 u# u9 J2 ^
5 i/ Z) w, K1 k- q! L公元805年,唐德宗驾崩,久病的太子李诵即位,是为唐顺宗。历史的闸门轰然开启,一场名为“永贞革新”的风暴席卷朝堂。这短短的一百四十六天,是刘禹锡一生中最接近权力之巅、也最接近理想实现的日子。
- x5 t' }7 x9 K$ P5 _
( \3 k+ R0 @) G! q4 N; a我们必须闭上眼睛,去感受那一刻他内心的激荡。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写诗抒发愤懑的御史,他成了历史的推动者。当一道道革新政令从他们手中发出时,他的笔尖一定在微微颤抖,那不是紧张,是兴奋。
. K- n4 h& t* `: T4 q( c) d' {- d
$ h2 y. v: g: ^, O, o& V! l想象一下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政事堂通宵达旦的场景。烛火摇曳,映照着他们年轻而坚毅的脸庞。他们讨论的每一个决策,都关乎帝国的命运。当他们决定“废除宫市”和“罢黜五坊小儿”时,他们脑海中浮现的,一定是那些被宦官强买强卖、倾家荡产的长安市民的脸。当他们着手削夺宦官兵权、抑制藩镇势力时,他们感受到的,是与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利益集团正面交锋的巨大压力与快感。史书记载,革新措施推行后,“市里欢呼,人情大悦”。这欢呼声,穿过长安的街巷,传到刘禹锡的耳中,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。那一刻,他会觉得所有的冒险都是值得的。他与柳宗元,这对“同榜进士”、“同朝为官”的挚友,并肩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,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。
* V* a4 {' I4 `+ p, _8 q, D. R6 ?1 R& [7 u7 o0 ^
然而,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。他们的最高支持者唐顺宗,在即位前就已中风失语,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政治靠山。他们的锐意进取,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核心利益。宦官们控制着神策军,那是悬在所有改革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( d- H# S, |5 v' }7 H3 `6 P# [( C
) Y+ f4 Z( O7 A, d- t: S3 o; m改革的后期,刘禹锡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焦虑。他或许在某个深夜,从堆积如山的文书中抬起头,看到窗外沉沉的夜色,会感到一丝寒意。他看到的是一个与整个旧世界为敌的自己,他们的力量,终究只来源于皇帝一人微弱的信任。他们的改革,像一场在烈火上烹煮的盛宴,香气四溢,却随时可能锅毁人亡。
d: d0 e+ f y# ~% x' X7 W
* n' z* t+ [/ {, ^这一时期,刘禹锡没有留下太多诗歌。他的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这场政治豪赌之中。他的诗,就是他参与起草的每一份诏书,他推行的每一项政令。他的情感,不是通过文字,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的。那是一种燃烧的、奋不顾身的、带有强烈使命感的情感风暴。
3 I* q, `3 D2 V" L" g
' {1 H- D2 P& w6 b$ I: j; ]0 _最终,风暴在公元805年八月戛然而止。宦官俱文珍联合藩镇,策动了一场宫廷政变,逼迫病重的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,史称“永贞内禅”。王叔文被赐死,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八位核心成员,则被尽数贬为偏远州司马。史书用一个冰冷的词汇为他们定了性——“二王八司马”。
5 }8 A- I$ Y* i5 o3 L$ D& z4 a( |! ?
巅峰之下:梦碎之处,长夜之始/ i h- h& S2 c3 V2 Y
; E3 @ ?. o2 d9 t/ m. X5 d4 O9 v
长安的梦,碎了。那柄闪耀着朝露光芒的利刃,在与顽石的第一次碰撞中就已崩裂。对于三十三岁的刘禹锡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,更是一次信仰的崩塌。他曾相信,凭借才华和热血可以重塑乾坤,但现实却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。
& `! b: _' j3 Q& }# Q/ C$ U. c8 G# e7 O+ V, `) x; d
当贬谪的诏书送达时,他与柳宗元这对曾经的政治盟友,此刻成了患难与共的“贬臣”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最后一次在长安的对视,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光彩,只剩下无尽的苍凉和对彼此命运的担忧。他们将要被抛向帝国的边缘,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、充满未知与凶险的世界。, v5 H; U$ L' U
* V `4 H5 Y+ Q8 a/ F+ N( _4 I
从权力中枢到蛮荒之地,从帝都的万众瞩目到天涯沦落人,这巨大的落差,是理解刘禹锡后半生所有情感的起点。长安的繁华与理想,像一场短暂而绚烂的烟火,在他生命的天空中炸开,留下的,是漫长而寒冷的黑夜。这黑夜,将长达二十三年。而他与这个世界最初的、也是最激烈的对抗,才刚刚开始。
8 \7 q8 I- p6 v9 ~
) {4 Z3 x6 f* R' ~' Q# A第二幕:巴山楚水——一个灵魂的淬炼 (805-815)7 i; u. ?! V2 K
1 k# G6 B7 g0 n. @ @, r: E% n
幕布拉开:朗州的风、瘴气与悲歌9 L* c: T7 F: ^5 W$ Z7 }. t4 c5 S8 f O
) f% d0 B7 n W! Z/ R5 |4 j9 P, _
永贞元年(805年)的初冬,刘禹锡抵达了朗州。这个位于今天湖南常德的地方,在唐代是名副其实的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。这里没有长安的亭台楼阁,只有简陋的茅舍;没有昔日的同僚挚友,只有陌生的方言和猜疑的目光。他名义上是“司马”,实际上是一个被严密看管的囚徒,政治生命已被宣判死刑。更残酷的是,朝廷随后下达诏令,宣布“二王八司马”等人“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之限”,彻底断绝了他们短期内重返权力中心的一切希望。" A+ s. P& c) ]6 q& u
/ D: m5 c6 X: r: [' M$ [这一时期的主导情绪,是灭顶的绝望。刘禹锡后来形容初到贬所的心情是“鸷禽毛翮摧,不见翔云姿”,一只羽翼被折断的猛禽,再也无法想象翱翔云端的姿态。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失意,更是精神上的囚禁。
( L/ B0 R2 q, _- X& F5 G! {3 c
7 I0 S" R* |: ~2 v4 ^2 l5 ~' s6 X7 K9 |然而,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。在这片蛮荒之地,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重创——他的妻子不幸亡故。史料对刘禹锡的家庭生活着墨甚少,我们无从得知他妻子的姓名,也找不到像元稹《遣悲怀》或苏轼《江城子》那样泣血的悼亡名篇。但这沉默,或许正说明了悲痛的深重。在一个举目无亲的流放之地,失去相濡以沫的伴侣,那种孤独与无助,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描摹的。我们可以想象,在无数个湿冷的夜晚,他独坐寒灯之下,耳边是凄厉的猿鸣,心中是无法言说的“丧妻悼亡之痛”。+ x# ^2 T0 K, l; v, z; ^
5 }5 G- q% J) q. A2 o9 Y8 M政治理想的破灭与家庭的破碎,双重的打击将他推入了人生的谷底。正是在这样的谷底,刘禹锡的性格中一种最核心的力量开始显现。他的乐观,并非天真,而是一种在彻底认识到生活残酷之后,依然选择与之对抗的意志力。他没有沉沦,而是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自我救赎。1 |5 y y V2 u3 b7 {
! ~* D9 @0 Y. A7 O7 u9 w朗州十年:在废墟之上重建精神家园' G3 K/ H3 x& Z0 ]: P
1 u) l. ]* k8 z8 q+ L. x
在朗州的十年,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型期,也是他精神世界重塑的关键时期。他用两样东西对抗着绝望:诗歌与友情。
9 w! r w# L+ O1 _ Y7 Y3 {) z$ V$ I- D9 E ^1 A
第一声反抗的呐喊:《秋词》
. h6 T' v. ^$ u! n; S+ \% g
& W' f; _5 ]$ T) r$ m朗州的秋天,必然是萧瑟的。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落叶的气味,沅江的水汽带着寒意。对于一个贬谪之人,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是最自然不过的情感流露。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他:你的生命也如同这秋天,正在走向凋零。
1 w% X, b1 l8 g9 C: x& G
' r L8 L+ n: f% W3 b! n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。刘禹锡独自登上德山,或是徘徊在枉渚岸边。他看着枯黄的草木,听着悲切的猿鸣,内心的悲凉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他完全可以写出一首哀婉动人的诗,博取后世的同情。但他没有。就在那悲秋情绪达到顶点的瞬间,一股强大的逆反心理,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骄傲,从他心底喷涌而出。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:秋日的天空,因为洗去了春日的浮华和夏日的躁动,反而显得更加高远、更加清澈。一只仙鹤,冲破云层,直上云霄。那一刻,他与那只鹤产生了强烈的共情。那不是孤独的鸟,那是他自己不屈的灵魂。于是,他提笔写道:
, ?. f2 `2 P* y% ~: y% I
8 Z6 Z4 ~5 b6 {* {) O; @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 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+ F# K9 m b) ]: |. a6 A. N3 _+ x7 I0 k* Z% t" m8 g
这首诗的“诗眼”,是那个“言”字。这不是简单的“说”,而是“宣言”、“宣告”。这是刘禹锡在精神上与整个悲秋传统、与自身悲惨命运的决裂。他在宣告:你们都认为秋天是悲伤的,但我,刘禹锡,宣告它比春天更富生机。当他写下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时,他写的不是景,而是心。那只鹤奋力“排”开云层的动作,正是他内心对抗绝望、冲破精神枷锁的写照。这首《秋词》,是他吹响的第一声反击的号角,是他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标志。
8 [& u- o. v0 v2 b: ^: g* l
( b. E, j5 [ [9 J, |+ j在民间寻找新的生命力:《竹枝词》
3 S) o2 N$ @) `1 n; S' x1 b6 t3 N6 x& r" T; ~( ?
被剥夺了士大夫身份的荣耀后,刘禹锡开始将目光投向他周围的普通人。他深入乡间,饶有兴致地倾听和收集当地的“民谣俚音”。那些被称为“竹枝词”的民歌,充满了原始的、鲜活的生命力,吟唱着当地男女的爱情与生活。
* I9 n7 A' ]& A9 r2 G+ d
+ z) n7 _! {9 A: J/ u' z想象一下,刘禹锡坐在沅江边的吊脚楼里,听着船家女用清亮的嗓音唱着那些质朴的歌谣。歌声里有少女怀春的羞涩,有劳作的欢快,有对情郎的思念。这些情感如此真实、如此直接,与朝堂之上虚伪的客套、权谋的算计形成了天壤之别。他被深深地打动了。他意识到,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,生命以一种更本真的形式存在着。他不是以一个猎奇的眼光看待这些民歌,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,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。他开始模仿、提炼、再创作,将七言绝句的格律与民歌的活泼巧妙地结合起来。于是,一批全新的 《竹枝词》诞生了:
; a X0 O" c) v( `4 S4 D$ T
7 w: i. R1 W6 i7 l% ^' D4 C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。 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( a5 j# O( x$ i1 k" z$ J
) z1 I$ r- b! s9 t" @% ^这首诗,表面上写的是天气,实际上写的却是爱情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微妙心理。“晴”与“情”谐音,堪称神来之笔。当他写下“道是无晴却有晴”时,他不仅仅是在记录一种民间情歌的巧妙构思,更是在进行一场自我疗愈。这首诗里,没有了政治的沉重,没有了人生的失意,只有纯粹的美和人性的温暖。通过拥抱民间文化,刘禹锡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出口,也为唐诗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长安的失意政客刘禹锡,他成了属于巴山楚水的人民诗人刘禹锡。
7 c6 o! d5 Q, A8 s4 \& {+ Z" U+ S: e' o6 W9 k9 X1 V8 B
精神的磨砺:淬火成钢,百炼为诗
$ h: l+ M' Y0 F0 a
6 m1 f- {6 D4 t; ~在这十年间,将他从绝望深渊中拉出来的另一股重要力量,是他与柳宗元的友谊。他们虽然身处异地(柳宗元在永州),但书信往来从未中断。他们一同探讨哲学,刘禹锡写下《天论》三篇,声援柳宗元的《天说》,共同批判韩愈的天命论,这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相互扶持。他们也相互慰藉,柳宗元在母亲去世后悲痛欲绝,是刘禹锡的信件给了他力量;而刘禹锡在困顿中,也从柳宗元的来信中获得慰藉。) P" }+ Y; }1 Q: ], N
+ k7 k1 U* k! N这十年,是一场漫长的淬火。朗州的烈火与冰霜,烧尽了他年少轻狂的浮躁,也洗去了他身上的官场尘埃。他失去了很多——权力、地位、妻子,但他得到的,是更坚韧的意志,更深刻的对生命的理解,以及一种全新的、更贴近大地和人民的诗歌语言。9 \4 W8 u: H: D0 U: Y. R1 l
% {' G/ K' |% g5 _6 \3 H4 k他不再是那柄锋芒毕露的利刃,他被锤炼成了一块百炼精钢,坚硬,沉重,且带着无法磨灭的伤痕。这伤痕,将成为他日后诗歌中最动人的纹理。' j1 F) b/ l, W7 \/ a; c
2 F# v' \1 q( S+ q5 k9 w: j
(未完待续)
; E h4 p9 w0 h/ k2 q: w r |
评分
-
查看全部评分
|